
“失智症”,一种渐进性认知功能退化。我们可能对这个名词并不熟悉,但我们熟知的“阿尔茨海默症”(更通俗的说法是“老年痴呆症”)是失智症的常见种类之一。
失智症是一种怎样的疾病?它与正常健忘的区别在哪?在失智症的早期和末期,患者到底在体验着什么?我们又该如何照顾失智症患者?
在下文作者尼奇·杰勒德看来,“失智症是对自我的一次特别的漫长告别……对于失智症,生命结束的时间会慢得令人痛苦不堪。”并且,失智症造成的记忆、语言丧失以及带来的羞耻感同样可能发生在不可避免走向衰老的我们身上。
下文是身患失智症的人及其照护者的故事。这些书写能够带我们走进失智症的隐秘之地,也能够帮助我们思考“人”的意义、“家”的意义,帮助我们面对衰老。
本文摘选自《记忆的重量》,经出版社授权推送,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

1
失智症很常见吗?
人们提起失智症就好像在谈论定时炸弹。
事实上,这颗炸弹在很久以前就已经爆炸,只不过是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悄无声息地炸开来:隐秘的破坏。
患有失智症的人通常会成为“失踪人口” —— 被重视独立、繁荣、朝气与成功,厌恶脆弱的社会遗忘和否定。
而他们只会提醒我们:我们都会变老,我们都会衰弱,我们最终都会死去。失智症是我们目前最恐惧的一种疾病。它是“痛苦的故事” ,而与痛苦一样,它会一直持续。
这种痛苦从个人蔓延到那些照顾、关心他们的人身上,甚至还会蔓延到他们的社区,乃至整个国家。
我们不能只是谈论“他们”了——现在是“我们”的问题, 应该如何面对这一挑战,成为我们人类集体的问题。
在高度重 视自主性和能动性的时代,我们迫切需要提出一些问题:我们 该为其他人做些什么,我们该为自己做些什么?谁比较重要?为什么一些人似乎没有另一些人重要?为什么有些人会被忽视、 无视、忽略和抛弃?何以为人?何为人的行事方式?
我们经常脱口而出“我们”这个词,它代表着集体、民主和合作。它要求发出集体的声音,正如政客们喜欢说的那样,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在同一条船上——嗯,是的,不过,有些人在头等舱,可以欣赏海景,晚餐时可以来一杯鸡尾酒,有些人在底层船舱,还有些人则根本看不见。
阳光不会照到他们身上,我们甚至意识不到他们和我们一样在船上。另外,还有不少人掉进了冰冷的水中,被无尽的黑暗吞没,而船上的乐队还在继续演奏。
那些我们看不见的人,那些我们不关心的人,那些我们不为之感到心痛的人,那些去世前一直被我们忽视的人……如果我的父亲生前是个重要人物,我想在他最需要关怀的时候,可能会受到不同的对待。

当然,他是重要人物,但只是对那些认识他、爱他以及与他的生活紧密相连的人而言如此。我们的系统和社会应该珍视每一个生命,这样,我们就不必为了拯救彼此而强调情感认同。
我们都有义务拯救彼此,甚至对我们的仇敌也不例外,因为世界为“我们所共同拥有”,我们需要分享和传承。没有你就没有我,没有我们就没有我。
我们最终都要依靠彼此,我们应该对每个人、任何人都持有热忱的、明确的义务 — 尊重他们不是出于爱,而是出于共同的人性。
我们都被思维局限所困。我们不可能看见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全貌,只能看到我们的注意力微光所及的封闭的一小部分。
十几岁的时候,我只会注意其他十几岁的孩子 ;怀孕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了其他所有孕妇,然后是婴儿,接着,我看到的世界到处都是小孩子和他们筋疲力尽的父母,然后到处是单亲妈妈……现在,我看见无数脆弱、惊恐的人,然而这只不过是因为我看见我的父亲是如此脆弱和惊恐。
我们无法看见一切,但也许我们可以学会对我们的盲视有更深刻的认知,并做出适当调整。
2
失智症到底是什么?
阿尔茨海默病会导致神经细胞死亡和大脑组织缺失。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脑会急剧萎缩,最终影响大脑的各个区域。不过,解剖一些大脑时会发现,虽然被解剖者已经被确诊患有阿尔茨海默病,大脑却未显示任何患病迹象,而有些被解剖者虽然没有认知障碍表现,大脑却严重受损。
肉眼可见的大脑退化与一个人的行为、感觉和交流方式之间未必有直接联系,这是因为大脑是在一个相互连接的网络中生活和工作。
观察大脑并不能告诉我们有关大脑的所有信息:大脑并不是独立存在,大脑存在于拥有特定生活的身体之中。运动、饮食、地理环境、职业、情绪和人际关系状态等因素,都可能影响一个人对大脑中层层叠叠、错综复杂的迷宫中所发生情况的反应。
解剖台上的大脑没有活力,就是一团毫无生气的米色物体,但通过活的大脑的神经图像,可以看到活跃的连接,以及各种神奇、神秘之处。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通过检测与血液流动相关的变化来记录大脑活动。这些既能显示静态,又能展示动态的图像就像北极光、珊瑚礁或开花的树,千变万化。

看着这些色彩斑斓的图案,仿佛看着沉浸在爱、恐惧、嫉妒与希望之中的大脑。但大脑扫描图像并不是直接记录大脑活动的照片,它们展示着大脑中最努力工作的区域。
这有点像从直升机上俯瞰纽约市,可以看见人群是如何在街道上穿行:你能看见人们在不同时间段的活动,以及对不同事件的反应,但你并不知道在纽约生活是什么感觉。大脑不反映心智。
尽管如此,因失智症而受损的大脑图像仍然令人沮丧 :绚丽的色彩中夹杂着死灰色的斑块。
3
它与正常健忘的区别是?
“像你这样年纪的人,会开始害怕记忆衰退。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会努力思考和记住一些东西。”
很多健忘和年龄相关,而非健康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都会开始健忘,这是衰老过程正常、自然的组成部分。失智症并不是自然现象,它是一种疾病。
不过,这中间也存在一个灰色地带,一种充满不确定性和令人不安的状态,那就是当健忘变得严重,如许多失智症患者所说的那样,有些事情似乎“不太对劲”。
当人们不可避免地衰老,却还没有被确诊失智症的时候,会走过一片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的沼泽地带,这是一个过渡阶段,一些人将其视为自然健忘的病态化,而另一些人则将其视为针对未来问题的善意提醒。
疾病和正常之间没有什么科学界限,我们可以划出界限, 但它们的确切位置则有赖于评估性判断。
克劳迪娅 · 瓦尔德提出了自己的疑问:“这是一片灰色地带。在这片灰色地带中,什么程度的治疗才算合适?人不断衰老,怎样才算‘正常’?”
她经常发现情况发生变化,生命的支柱不断被抽走 :夫妻中那个一直照顾有认知功能衰退问题伴侣的人去世了,问诊人进了医院,摔断一条腿,或是搬了家。“这些事情可能让之前隐藏的困境暴露出来。”

她还表示,抑郁症“可能是一种前兆和风险因素”,而且很难治疗。“衰老过程中会有巨大的损失 :失去伴侣、家庭、朋友、工作和健康,以及无尽的孤独感和对死亡的恐惧。”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诊断往往不是很直接,而且通常是亲戚或看护人最先注意到这种变化,因为我怎么知道我在日渐衰弱呢?
4
失智症初期的体验?
“你得了失智症。”
不论以怎样亲切、巧妙的方式说出这句话, 不论以怎样轻描淡写的方式说出这句话,这都是一种宣判。我们都知道自己会死,但我们并没有真正理解这一点,直到我们被判死刑。
失智症是一种绝症,它通常会缓慢发展,逐渐侵蚀心智对自身的感觉。
失智症的诊断往往是给予确认,而不是惊喜——面对不断变化的、模糊的、武断的界限, 跨越了一小步。什么都没改变,但一切又都有所改变。
这个人在确诊后的第二天和确诊前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所处的世界既惊人地相同,又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对于那些得不到支持和毫无准备的人来说,这个世界可能会带来难以言喻的恐惧。
寻求诊断所需要的勇气和毅力,来自病患本人和关心他们的人。这种勇气和毅力非常伟大,不应由病患本人独自承担。但现实却常常如此。
失智症悄无声息地慢慢潜入我父亲的生活,没有被打破的窗户,也没有刺耳的警铃声,只有夜里偶尔的沙沙声,楼梯上的咯吱声,各种东西从平常所在的地方消失又不被想起。
我不知道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起疑心的,不知道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的,也不知道是谁先起的疑心。
他的母亲年纪不算大的时候就得了失智症,他的姐姐也是如此。我父亲总是健忘, 这并不是失智症独有的征兆,但感觉很像,他的未来好像与其仁慈而健忘的个性融为一体。
他仿佛消失在自己的秘密世界里,没人能紧随其后。

雾色渐浓。他的茫然变成了一种迷惘。他的快乐(或许只是一种坚忍)被焦虑刺穿,这种焦虑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不时折磨他,哪怕在他身患失智症却仍“活得很好”的情况下也不例外。
“活得很好”这一笼统说法显然不足以概括全貌。时间会治愈一切,时间也会毁掉一切。每况愈下的日子里,没有一件事或特定事件让我们联想到什么。
当然,现在回想起来,我能辨认出那些信号。
他努力想要记住树篱中的一种花的名字,他拿着一杯茶的手开始颤抖。他又一次弄丢了助听器,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或是迷了路(但这种情况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他的车撞上了大门。他把钥匙落在了锁上。当我们问他时间时,他告诉我们板球比分(但他总是健忘)。当我在他脸上看到一种无法辨认的表情(但他总是有点难以理解,让人捉摸不透)。我们一开始并没有讨论这种情况, 什么时候才适合问出 :你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吗?你的记忆力是不是开始出问题了?
最后,我们都意识到出问题了。他去看了医生,进行了记忆力测试。虽然医生机智地运用各种安慰策略,但他最终还是收到判决——“你得了失智症”。
对我来说,这不是对胸口的一记重击,更像是轻轻一推,把他推过了那条可移动的线,从半信半疑变成确定无疑。事实上,我甚至不记得听过这个消息。
5
失智症为什么让人羞耻?
这种羞耻感会以多种形式出现,受影响的个人及其家庭都会产生这种感觉。
因为对这种病的污名化而感到羞耻,因为失去权力和控制力而感到羞耻,因 为身份被残酷剥夺、暴露出脆弱的自我而感到羞耻,因为随着 时间的推移疾病影响整个身体以致身体变成一个糟糕的漏水容器而感到羞耻,因为严重丧失尊严而感到羞耻,因为失智症患者反复陷入麻烦而感到羞耻,因为那些一直被隐藏的隐私一点点被展现出来而感到羞耻。
因为我们都是喜欢表演的人,我们学会了在生活的舞台上表演自己,但失智症给我们带来噩梦和屈辱,我们仿佛站在观众面前却不记得自己的台词,仿佛所有人都看到自己坐在马桶上,仿佛所有人都看到我们赤身裸体。
我们不仅身体赤裸,灵魂也变得赤裸裸:那是属于我们的不停颤抖的柔软的一部分,我们用尽一生试图保护它不受热衷于批判的世界的伤害,最重要的是,不受我们自己的伤害。

当人们谈论失智症带来的羞耻感时,往往与身体的衰弱有极大关系。它还与混乱密切相关。
当我们开始冒出污言秽语, 喃喃自语,哭泣,说出疯狂而混乱的话,心智变得失去控制和逻辑,失去控制的身体反应可能最令人感到沮丧和羞耻。
我们从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隐藏心事或只在私下说出某些事——这是自我无节制的滥用。当长久以来被严格监管的边界崩溃时, 内在就会以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方式出现。
“别担心,这是自然现象,只是你的身体出了问题而已。”我听到一名护士安慰病人时这么说。但身体绝不仅仅是身体。身体既是我们生活的地方, 也是我们生活的方式。
失智症患者还有一种额外的恐惧,那就是不知道被抹去记忆的那些时候发生了什么,只留下模糊的不安印记。发生了一些事情。发生了什么?我做过什么?人们看到了什么?很可笑吗?我很可笑吗?
照顾失智症患者的人通常会与患者共同完成“虚构”任务,尤其是当这些看护人是其伴侣或配偶,并且已经建立了互相支持的关系。
毕竟,他们参加同一场演出这么长时间了,双方既是主演,也是彼此的观众。看护人会给他们所爱的人找借口,为他们打掩护,帮他们说完未说完的话,替他们编完故事,向别人解释,甚至共同承担假装正常的压力。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是一种善举:如果知道这种羞耻感源于脆弱的内在自我需要保护,那么你当然会用这种保护行为帮助所爱之人。
但是,在亲密关系中,另一个人的身份和自我的身份或多或少紧密相连,羞耻感可以像私密的传染病一样从一个人传染到另一个人。
我们不仅仅是和另一个人一起痛苦和焦虑,我们的内心也同样痛苦和焦虑,因为我们不知道双方的痛苦和焦虑何时开始、何时结束。

当人们面对失智症患者退缩并保持距离时,可能并不是因为他们缺乏同情心和同理心,而是因为他们感觉到极大的危险。
6
如何照顾失智症患者?
照护病人可能令人疲惫不堪,闹出笑话,也可能发人深省,还可能令人胆战心惊,时而感觉充实,时而觉得悲惨。在照护病人的过程中,照护人员的身体和情感融合在一起。
他们发现自己,也迷失自己;放弃一些事情,又承担一些事情;既感觉被削弱,又感到某种扩展;行为时而糟糕,时而得体;既为自己骄傲,又感到羞愧;既觉得永远做得不够好,又希望超出别人对他们的期望。
“护工”——应该有其他的词来称呼他们。
“无私”这个词几乎总是被用作褒义词——为了他人的利益,自愿放弃自己的愿望和欲望。在过去的一年里,我阅读了大量书籍,这些书的作者都欣然谈论着无私的照护,几乎是用虔诚或高尚的语言在歌颂这种行为。治疗的目的是为了康复,在社会上有很高的价值,而照护本身就是目的。一位作家将这一行为与英雄普罗米修斯和坚忍的西西弗斯的神话故事相提并论。
从功利主义角度而言,照护没有什么价值可言,我们应该从“契约”和“忠诚”角度来考虑这一行为。
照护过程中的互惠互利情况有限,甚至在失智症晚期,患者和照护者之间完全不存在互惠互利关系,照护者的成就往往存在于不被看见的细节:没有褥疮,没有营养不良,没有摔倒……不论结果如何, 不论得到怎样的认可,照护者都需要从照护行为本身中寻找意义。
他们是“心灵的守护者”,必须是“有信仰的人”。作家、护理学教授萨莉· 加多认为,照护是介入他人的脆弱与衰弱,并“打破自己”的过程。在这一相互破坏的过 程中,在治疗模式中被认为是有辱人格的行为(比如抬起、清 洗和喂食),反而成为“契约的纽带”。
这是一种纯粹的无私——介入他人的恐惧、失落和脆弱, 把自己的世界抛在身后,为了陪伴需要帮助的人而抛弃自我。这种无私行为高度重视自我放弃和忍受痛苦。
虽然对照护行为持有这种想法,承认了这项任务意义深远,并赋予其无法量化 的价值, 但与此同时也打击了自主、独立和自我这些观念。当然,“自主”这个词过于简单,“能动性”一词也是如此。
长大成人后,我总是随意说出这些话:坚持自己的立场,做我自己。真的能活得如此自由自在吗?我们生来就相互依赖,依赖是人类生存状态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人生的旅途中,作为血肉之躯,作为拥有身体和具象化思想的自我,作 为丰富而不断变化的人际关系网的一部分,我们是一种持续不断的脆弱体现。
也许,21世纪的世界已经变得过于专注自我保护,树立起太多界限。我们必须持续打破界限。照护他人和被他人照护是文明的组成部分。影响如何过好人生的最基本问题是人 际关系问题。我们在政治上、情感上和心理上都相互关联。
然而,然而……
7
晚期失智症面临着什么?
没有人从晚期失智症的国度回来告诉我们那里是什么模样。就像声呐显示屏上的脉冲光一样,他们逐渐变暗,直到无法被追踪,我们无法想象他们在寒冷、幽深的黑暗中正在经历什么。
那个躺在我女儿身旁的老妇人,一遍又一遍地喊着相同的可怕的话 :她是在激烈地经历过去的创伤,还是只是被一段记忆缠住了?

当我的父亲也开始说“我必须重返大海”时,我不知道他在脑海里看到的是浪花飞溅的海面、海雾和晃动的白帆,还是这些话只是一些记忆的痕迹,只是一个濒死的意识随意迸射出的最后的火花。
思考失智症的晚期阶段就是思考人类究竟是什么,就是承认个体精神在本质上的孤独和隔离。
我们一生都在与他人建立联系,试图把自己的生活想象成他们的生活,试图交流我们自己的感受——在自我之间的巨大鸿沟上架起脆弱的桥梁。
爱上他人就是相信我们可以被他人了解,真正被他人了解,反之我们也可以了解他人,通过强烈的依恋和欲望的融合与他们一起感受——两个故事合二为一。
我们可以伸出手拉近彼此,讲述我们的故事,倾吐心声,将秘密作为礼物赠予对方,但我们永远无法进入另一个人的精神世界,无法通过他们的眼睛看清世界的模样,无法感受到他们身体或心灵的具体痛苦。最后,我们对彼此而言都很神秘。
8
如何与失智亲友告别?
失智症是对自我的一次特别的漫长告别。
对大多数疾病而言,死亡来得很快。而对于失智症,生命结束的时间会慢得令人痛苦不堪。失智症患者可能有充足的时间思考自己的死亡,照顾他们的人甚至有更长时间思考这个问题,通常有许多年供他们想象、准备和彩排。
他们有一种预期的、模糊的悲伤,得以提前哀悼自我或所爱的人。
失智症发展到最后阶段,心爱的人可能还活生生地站在眼前,却又处于缺席状态,有力地提醒着我们自我的失去。
在漫长的走向结局的过程中,他们逐渐被拆解,但仍像幽灵一样纠缠着我们和他们自己:他们不再认识镜子里的那个人,或是把镜中人认成他们死去的父母、他们的影子替身。
哀悼一个还活着的人会引发一种复杂而特别的痛苦,而且常常会带来负罪感 :哀悼一个还没死的人就是在把他们送上死亡之路。

失智症患者去世时,他们的死亡对他们自己而言往往既是一个失去的过程,也是一种解脱,他们已经被疾病击垮,并且忍受了足够长时间的痛苦。
他们的死亡对那些深爱着他们、关 心他们的人而言,同样既是失去也是解脱。我们会说“他们已经活过了他们的时代”。我们还会说“时候到了”。
如果一个人在过去十年里一直照顾自己的伴侣,为他洗澡,喂他吃饭,为他收拾烂摊子,为他哭泣,远离他,爱他,恨他,对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感到厌倦,被它困住,筋疲力尽,对缺乏互惠的关系和自我的丧失感到绝望,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还不希望他离开,不希望这漫长而艰难的旅程结束,这个人一定得是个圣人。
我们要找回自己的生活。
他们死后,悲伤无孔不入。因为即使我们说失智症患者已经“走了”,变成了“空壳”,“不再是过去的样子”,是“行尸走肉”,但当他们死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们终究还活着。
他们终究是他们自己,尽管他们已经失去自我。
去世前几周,我父亲脸上仍然会露出他的招牌微笑,在其他人脸上看不到他的那种轻笑,这个活生生的父亲与我在殡仪馆的小房间里看到的那个死去的人之间的差异大到让人无法形容。
人们曾告诉我世界上存在一个频谱:人们在一端拥有明确的自我,但他们会逐渐滑向自我丧失的一端,比如最后陷入昏迷状态时,他们可能还有呼吸,但其实已经不复存在。除了身体,什么都不剩了。
我的一个朋友不得不决定在什么时候关闭维持其伴侣生命的机器:他处于植物人状态,毫无疑问,这是她唯一可以做的事情。
但这是一个严肃而痛苦的决定。这意味着:这条生命结束了。
永远不会再有了。不会再来了。
这就是生命的奥秘。一个人可能什么都没有了,没有记忆,没有语言,意识不到自己存在于这个世界。然而,在他们破碎的身体里,却藏着他们不可磨灭的本质。
德里达曾写道:“活下去,是哀悼的另一种说法。”

活下去是一件复杂的事情。成功的哀悼也是失败的哀悼。
悲伤是一种记忆、一种忠诚, 也是一种陪伴死者的行为。恢复是一种必要的背叛,一种独自前行的行为。
许多失去亲人的人在经历幸福回归的时刻,或是意识到自己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想起死去的心爱之人时,会感到内疚。死去的人成为被遗忘的人,即使是短暂被遗忘。
而我们必须忘记, 让死去的人逐渐沉入我们的记忆深处,在那里, 我们不会经常感觉到他们。如果我们不这么做,而是停留在强烈的令人惊骇的悲伤第一阶段,我们会疯掉(当然,有的人确实会被困住,会发疯)。
死去的人仍然活在我们心中,但我们并不会一直想起他们,因为他们已经成为我们的一部分,融入我们的身体。
他们永远缺席,永远存在于过去,同时也永远存在于现在和我们的未来。这就是哀悼,一项痛苦、旷日持久、庄严而重要的工作。
我们将死者召唤到我们身边,以此认识我们自己的死亡。
无论死亡的过程多么平静,无论跨越的时间多么短暂,死亡从来不是一件小事。只要呼吸停止,就像轻轻吹了一下羽毛,整个世界就消失了。
然而,死亡也能修复一个人,尤其是当这个人被失智症破坏的时候。一旦他们死去, 他们不再只是衰老、脆弱、有病的人,他们不再只是糊涂和健忘,不再只拥有残破的身体和衰弱的精神,不再不是他们自己。
因为他们已经离开我们,他们可以回到我们身边,成为他们曾经的自己。
年轻,年老,介于两者之间的自己。强壮,脆弱,介于两者之间的自己。我们常常会神魂颠倒地爱上所有这些自己,我们明白他们是如何包容众多的自我。
这就是好的葬礼所能带来的东西:完整的自我再次被记起、恢复和弥补的感觉。

本文摘编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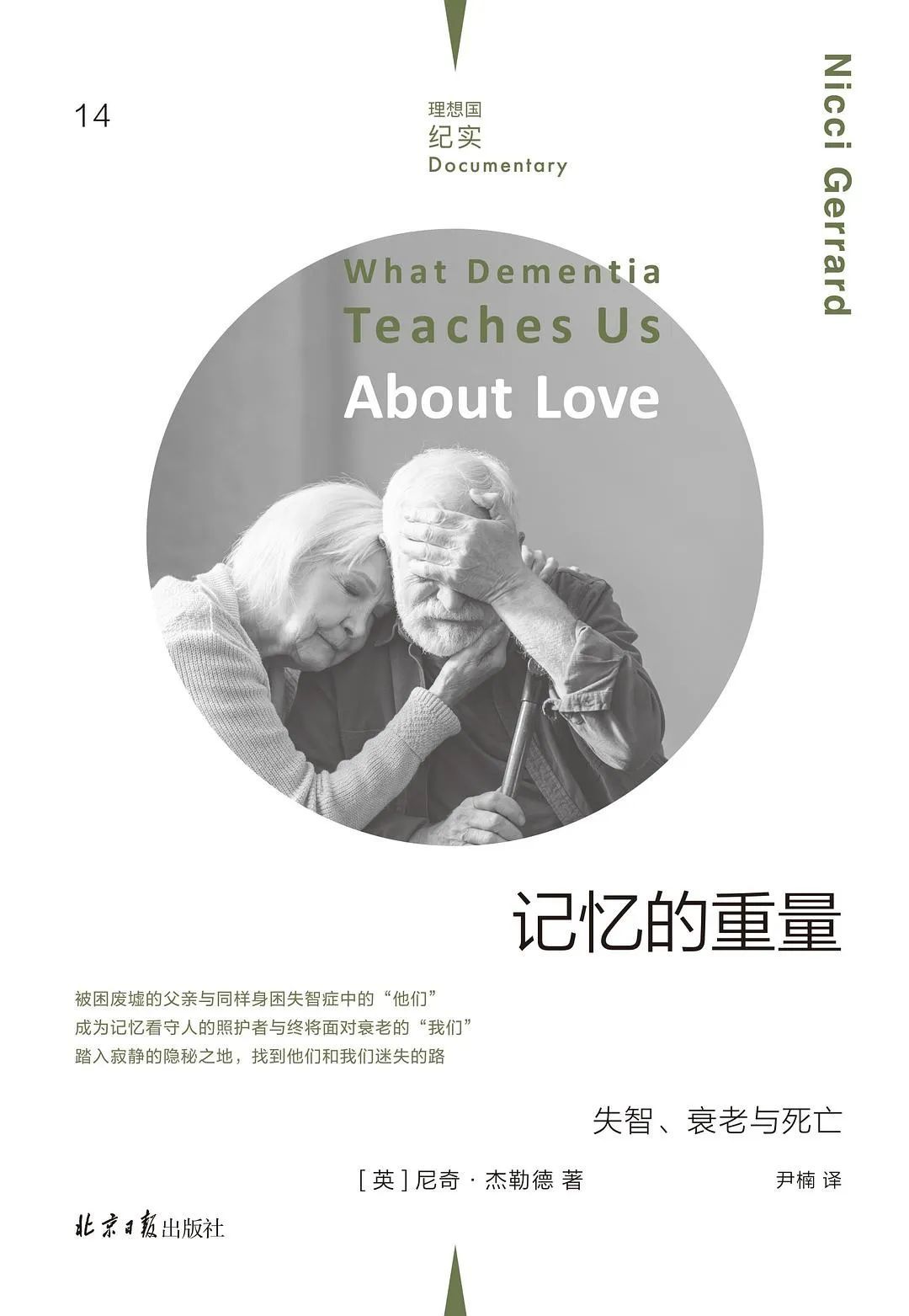
《记忆的重量》
副标题:失智、衰老与死亡
作者:[美]尼奇·杰勒德
译者:尹楠
出品方:理想国
出版社:北京日报出版社
出版年:2023-7
相关:
一意孤行,前途未卜,还是回家吧星期天文学·金特周五好,这里是「星期天文学」。也许有读者还记得这个名字,它初创于2016年,是凤凰网读书最早的文学专栏之一。这几年,我们与网络环境相伴共生,有感于其自由开放,也意识到文字载体的不易,和文学共同体的珍稀。..
当女人想要一间自己的办公室 | 爱丽丝·门罗爱丽丝·门罗被誉为“加拿大的契诃夫”,她也是第一位加拿大籍女性诺贝尔奖得主。1968年,37岁的门罗出版了她的第一本书、短篇小说集《快乐影子之舞》,讲述加拿大乡村小镇各个角落的生活片段,探索青春的回忆、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