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两年诺奖颁奖前后,残雪的名字就会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之中。今年尤其如此,她的长篇小说《新世纪爱情故事》今年在瑞典出版,译者正是当年翻译莫言作品的那位,出版后引起瑞典各大报刊媒体的讨论。诺奖结果公布前的几个小时,残雪高居博彩公司赔率榜第一名。然而,一旦获奖者不是她,她的名字便再次在国内消身匿迹。
残雪是谁?如果不是因为诺奖,知道她的人并不多,读过她作品的人更是少之又少,这样一位被认为是最有希望得诺奖的中国作家,居然让中国读者感到如此陌生。
在国内,她从未获得任何重要的文学奖,豆瓣上残雪书籍的评分普遍在7分左右,在文学评论界,研究她的人也比研究余华、莫言的人要少得多。
反观国外,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中唯一精通中文的汉学家,已经去世的马悦然称残雪是“中国的卡夫卡”,美国学者、作家苏珊·桑塔格称残雪是中国最好的作家。在美国,几乎所有学习创意写作专业的学生,都需要研读残雪的小说。日本有专门的残雪研究会,是日本唯一以中国当代作家名字命名的研究会……
为何一位长居国内的纯正中国作家,在国内和国外受到如此不同的待遇,残雪为什么在国外如此受欢迎。也许读完下文,这个疑问讲得到一些解答。
以下为中山大学教授郭冰茹、人民大学教授杨庆祥、残雪瑞典文翻译刘长征、残雪英文翻译冯安仪在“中西文化语境下,残雪的小说世界”分享会上的对谈实录,凤凰网读书经人民文学出版社授权发布,篇幅所限,内容有删减。
01
所有读创意写作的美国人
都会读残雪的小说
郭冰茹:今天很荣幸邀请到残雪小说的两位海外译者,冯安仪女士和刘长征先生。一方面我们很想知道残雪在海外的翻译和传播情况,另外我们也很想了解国外读者如何看待残雪的作品。

△图源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中西文化语境下的残雪小说世界”直播截图。 从左到右、从上到下依次为: 郭冰茹,特邀嘉宾主持,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杨庆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刘长征,残雪的瑞典文翻译; 冯安仪,残雪的英文翻译
刘长征:我可以说一下瑞典这边的情况。瑞典是一个很小的国家,没有很多人从事中文翻译事业,所以到现在为止,残雪的作品出版了两部长篇,还有一些在杂志上发表的零碎的短篇。长篇是我2012年翻译的《五香街》,还有去年出版的《新世纪爱情故事》。《新世纪爱情故事》是大出版社出的,由著名翻译家乔安娜翻译,所以得到了蛮多关注,六个不同的纸媒都在评价这本书,这算很多了。
冯安仪:说到残雪在美国的印象和影响,我非常乐观。几乎所有专门学习创意写作的美国人都会阅读残雪的短篇小说,她的长篇小说最近几年也很受欢迎。除了文学界和学术界之外,纽约有献给残雪的艺术展览、戏剧表演,美国出版译本的市场还是很窄,竞争性挺高,残雪能在美国成功很了不起。

△图为2021年位于纽约的艺术展“未来已至”展品之一,据介绍此展览灵感来自残雪小说《新世纪爱情故事》
郭冰茹:我2010年在美国斯坦福访学,遇到一个比较文学系的博士,美国人,他跟我说正在翻译一篇残雪的短篇小说,我问他为什么选择残雪的作品翻译,他说因为她很独特。
你们觉得残雪的小说是独特的吗?它的独特性在哪里?如果跟同时代的比如瑞典的现代作家,还有美国以现代派为主要表达方式的作家相比,残雪的特点在哪里?
冯安仪:一般来说文学创作都是情感实践,但像残雪的小说《激情世界》这样切入中国式实践确实独一无二,残雪说中华民族是实践的民族,所以她的小说是对她理想的一次实践。小说中的人物背景亦如此,是精彩的实践,每一位进入小说,读者都是进入小说营造的乌托邦境界中,在实践中展示自由的张力。
刘长征:我开始喜欢残雪的作品是十几年前,瑞典有一个国际图书馆,有很多不同语言的书,我当时在那里翻了一些书,很偶然拿出残雪的《五香街》,读了第一句话,“在我们五香街上,关于X女士的年龄至少有28种说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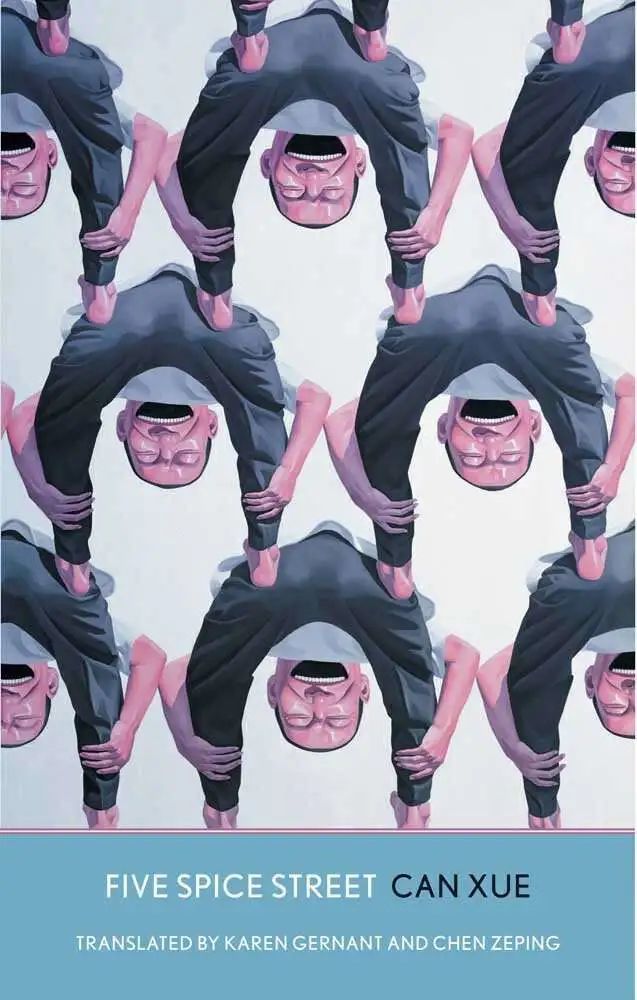
△《五香街》耶鲁大学出版社版本
我觉得这个东西太幽默了,必须借回来读,然后就爱上了这个作家。她的风格独特,读完就让我有翻译的冲动。我自己开始翻译这本书,没有跟任何出版社联系,也没有跟作家本人联系,自己就开始做了。确定要出版这本书以后,我在上海开始跟残雪老师有一点交流,突然有一天收到一个很大的包裹,是残雪寄给我的作品,然后我开始钻研这个文学大户。
她的文学有一个很明确的发展过程,从最开始那些短篇,《五香街》这些都是很消极的内容,不像安仪说的乌托邦的世界,它是相反的,描述的是抑郁的世界、抑郁的形象。慢慢地,随着她挖掘内心世界的过程越来越成熟,好像得到了净化,里面的精髓出来了,变成乌托邦的世界。
我开始意识到这个过程,是由于读她的文学评论和文学批评,她的文学批评不是关于中国作家的,都是关于西方的经典作家,所以我那时候突然有冲动开始研究西方的经典作家,之前我喜欢的基本都是中国古典文学。我发现她的文学作用可能就是做东西方的文化桥梁,她自己就是这样描述的。
郭冰茹:安仪老师刚才讲在美国学习创意写作的学生会大量地阅读残雪,但是中国大学里面创意写作的学生,好像读残雪的不是太多。
杨庆祥:比较少,中国创意写作专业的学生更喜欢读像门罗、福楼拜、卡佛、耶茨、菲茨杰拉德的作品,我们特别强调怎么讲好一个故事,把故事讲的特别有意思。但是以后可以考虑让他们也读一读残雪的作品。

△纵然蜚声海内外,残雪还是大众眼中最难以接触的那一类作家,作品晦涩难懂、难以捉摸。
郭冰茹:所以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中国大陆创意写作的学生会比较多的读西方的像福楼拜这样的作品,美国创意写作的学生比较专注读残雪的作品。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阅读错置的情况?安仪老师您有什么回答吗。
冯安仪:我从中国的豆瓣上看到年轻人对残雪作品的评价,他们中的一些人表示,想要努力成为小说中描述的那类人,那类人是什么人?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的人。在我们美国的文化与文学语境下,残雪独特的方面会吸引我们。
郭冰茹:中国当代文学史里把残雪视为先锋派作家,您觉得残雪的这种表达方式或者她所呈现出来的小说世界,跟您所理解的西方的先锋派或现代派,他们之间相同性更大还是相异性更大?
刘长征:读残雪对自己创作的描述时会发现,她想描述的是自然本身,而不是社会现象或比较狭窄的文学性的东西,她小说精彩的原因在于,它就是自然本来的面貌,它代表着美的最高境界,也代表着大自然最本质的东西。我比较提倡从这些方面去了解残雪的创作,而不是跟其他的当代中国作家比较。
郭冰茹:庆祥,听了两位译者对残雪的分析和感受,对照国内读者对残雪的阅读体验,您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
杨庆祥:两位老师对残雪的阅读和接受,确实跟国内不太一样,在不同的语境里对作品的理解、解说和解读确实有很大差异。
残雪在1985年左右,是一个影响很大的作家,大家对她的认可度、评价也很高,但是到了90年代,中国先锋文学其实有一个转型,很多作家,比如余华,部分放弃了先锋的书写方式,用一种相对来说更加传统、更加现实主义的表达方式,赢得了更多的读者和更高的评价。但残雪是一个非常倔强的作家,是一个不愿意轻易改变自己的人。她对自己的艺术理念和创作的方式都非常自信,认为那是真正能够表达她自己对这个世界、对中国、对文学的理解的。
在大众的领域,比如她在美国被很多创意写作专业的人阅读,这个消息很难被传递到中国读者这里来,但是诺贝尔文学奖是特别重要的世界性大奖,中国读者也关注这个奖,所以每年残雪在中国影响最大的时候,都是诺贝尔奖要揭晓前一两周,因为大家都在说残雪又进入赔率榜了,中国的很多媒体也会加入到这样的话题表达中,所以大家有会知道残雪还在写,可能写出了很好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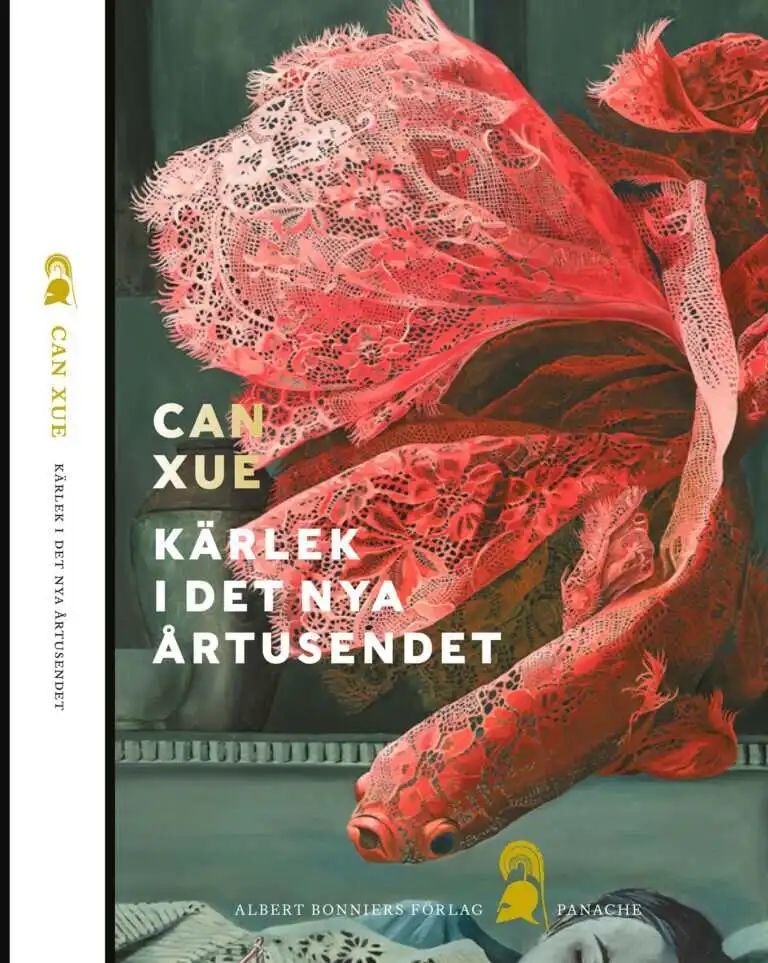
△《新世纪爱情故事》瑞典版封面
但非常遗憾的是,大家还只是把她作为一个现象,而没有真正静下心来阅读她的作品,具体去研究残雪的作品究竟给我们提供了什么不一样的东西,这是目前中国的读者、研究者对残雪的接受和阅读中非常脱节的情况,我们知道残雪这个作家,对她也有了一个比较感性的认识,但她到底在写什么,好多人其实根本不知道,甚至没有这些海外译者了解的清楚。
02
从人间地狱到乌托邦
残雪的小说越来越通透
郭冰茹:庆祥,请您给两位海外译者分享一下80年代的中国文学,以及残雪是怎样登上文坛、变成文学界一颗耀眼新星的。
杨庆祥:主要还是当时历史的大趋势,70到80年代的转型过程中,中国当时有几个文学写作的潮流,一是伤痕文学,当时非常流行,写文革的创伤,代表性的作家有卢新华、刘心武。但这个潮流到1980年左右差不多就结束了,后面开始所谓的改革文学。
改革文学写中国社会变革过程中涌现出来的新事物、新现象以及面临的问题,比如作家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当时在改革文学里非常重要。张洁也是一位女性作家,两次获得茅盾文学奖。改革文学和伤痕文学主要是在表达的内容上与以前的小说相比有一些变化。
1985年左右,有一种对文学形式变革的渴望,包括强调向内转,强调写作的语言。以前我们对语言不是那么重视,重视写作的形式感,所以当时现代派文学非常流行,在当时叙事的谱系里被认为是具有更高美学价值的文学类型。现代派文学有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在这前后有一批更年轻的作家涌入到文学场里面来,他们提供了一批全新的作品,像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莫言的《红高粱》。
残雪也是这时开始进入文坛,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她80年代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过一个作品,叫《山上的小屋》,是很短的短篇,可以看出她的先锋性和实验感。没有特别具体的人物,也没有特别具体的情节,整个表达是非常含混的状态,里面有很多在我看来跟中国历史和创伤有关系的东西,她用一个很小的短篇把它呈现出来。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残雪曾辞去教师职位下海当“个体户”
当时残雪的这些作品给人感觉耳目一新,同时又跟当时中国当代文学求新求变的潮流契合,她一下子被大家记住。
这里有一个细微的区别,刚才长征老师从比较普遍的,比如美的、大自然的角度解读残雪的作品,但我是一个中国读者,我会从她的作品里面读历史,读它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在不同语境里面进入的角度不太一样。但正是不同角度进入,才会让残雪的作品越读越丰富。
郭冰茹: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比起那些后来回归到现实主义表达方式的作家来说,残雪的写作表达方式仍然那么先锋,但残雪也是求新求变的。我自己的阅读感觉来说,从《山上的小屋》到《激情世界》,她的变化挺明显的,我觉得残雪也开始注重讲一个故事了。
我想问一下长征老师,您觉得残雪的这种变化,跟她本身的文学观念、对艺术的追求有关系吗?
刘长征:她的艺术观念和创作方式没有一点变化。她自己经常说,“我写的东西是大自然逼我的。”大自然可以逼一个人写作,这个有点神秘,我们没有她的个人体验,比较难了解。但作家和艺术家的一个概念是,比如古罗马会把艺术家当做是先知,他就要说出某一个神想传达的信息,艺术家或者诗人被当做超现实的、形而上的世界的解读者和发声人,这在历史上是固有的现象,历来都有读者用虔诚的态度去读这些伟大的诗人和艺术家,甚至有一些会用读宗教《圣经》《古兰经》的眼光去看伟大的诗人。
要怎么读?有一个12世纪的伊朗哲学家,他说,“我读《古兰经》是把它当做上帝写给我一个人。”你要把宇宙的创造者、造世主传达的信息当做是写给你一个人的。
这些艺术形象在残雪脑子里,她认为是大自然赋予她的东西,让她必须这样写,不能用别的方式去写。至于为什么她从80年代地狱的意象转变成现在乌托邦的意象,这里有什么原因?可能纯属一些个人的因素,我们很难去猜测。
她的可读性提高了很多,最近的《激情世界》差不多像青少年小说一样,而且讲的都是谈恋爱什么的,也有一些生活的困难,她用她特殊的角度去写。这个小说里明显放进了很多她对于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概念,她明显想写一个艺术化的生活。“如果每个人的生活里都有艺术,如果我们把艺术放在第一位,我们的生活也会变得更精彩。”差不多是这样的写作态度和人生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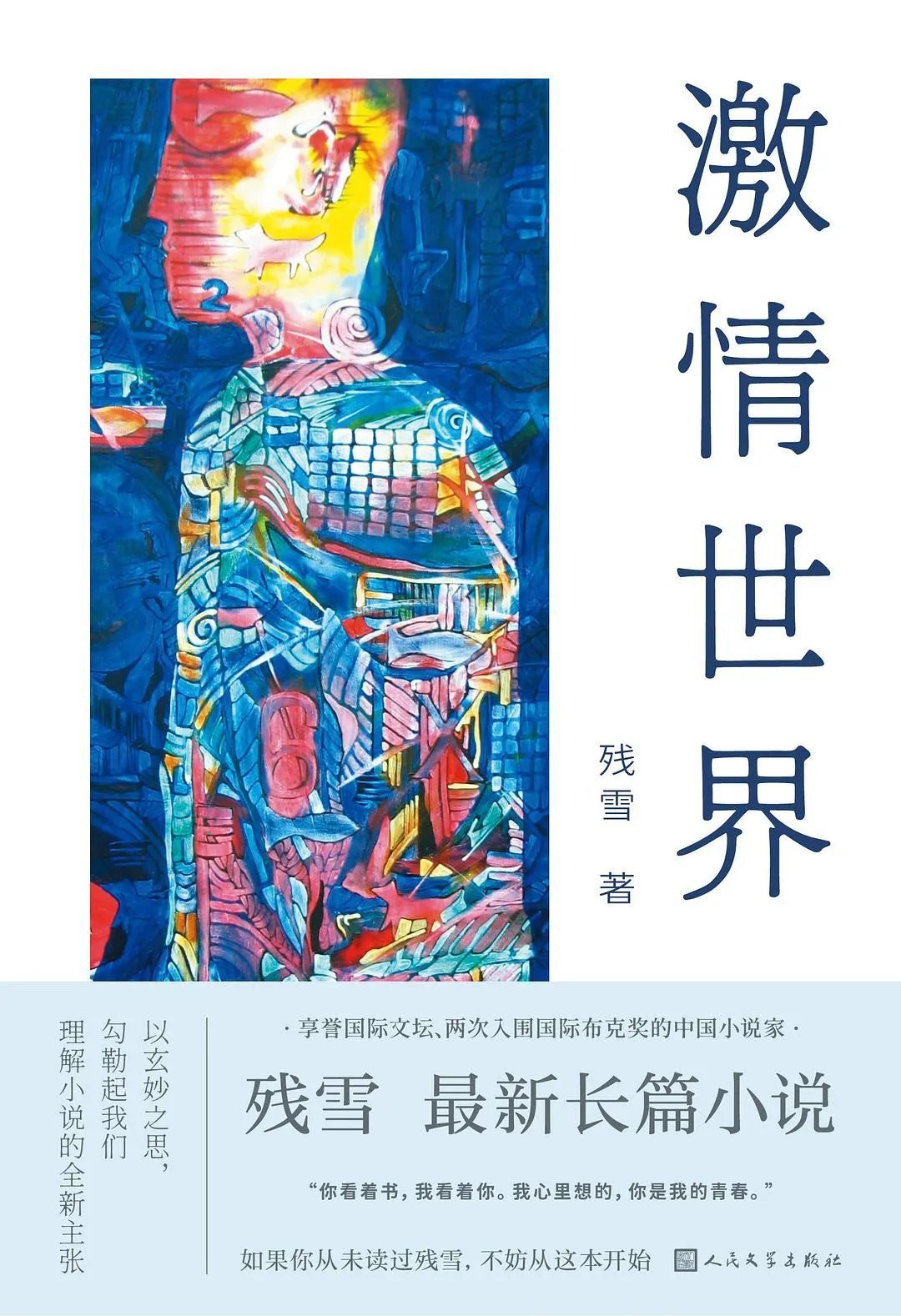
△《激情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11月出版,英文和瑞典文的翻译也在同步进行中
可能在80年代她刚开始写书时,对这个崇高理想的了解是潜意识的,还没有那么清楚,通过不停地发掘,她发现它是一个这么美的东西,她的作品也就随之越来越长,越来越整体化,不那么零碎。
冯安仪:我很同意郭老师说的残雪的改变,还有杨老师说的她的坚持,我觉得这些都是残雪的特点,都是她不断写作的突破。
现实中的人都是不完美的,但这种不完美都能突出某些乌托邦个性的底色,这是我们为什么需要本质性写作。残雪的长篇,包括《最后的情人》《新世纪爱情故事》《边疆》等都是关于人性本质的写作,而最新的这部《激情世界》则有种遁入的通透感。她以亲近读者和日常生活的新态度,讲述追求自由的人的故事。
我们说残雪是先锋作家,先锋理论一开始来自欧洲20世纪的艺术家运动,彼得·伯格的先锋理论表明,先锋艺术家试图打破艺术和生活的分界线,把这个理论跟残雪不断的突破联系起来是理所当然的,但不一定是真实。残雪一贯主张将文学与生活一体化,这种立场在《激情世界》中达到了极致。这种直接从人性本质开始的干净写法,我从来没有在当代小说中遇到过。
郭冰茹:所以她的这种写法特别吸引您?
冯安仪:是的。
郭冰茹:上课的时候,跟学生讲当代文学史,讲到80年代,发现如果想要给学生描述残雪《山上的小屋》《阿梅在一个夏天的午后》这样的短篇小说,是非常困难的。
在《激情世界》里,她讲了几对青年,比如小桑和黑石、寒马跟小月、雀子和李海、余叔跟小麻,他们之间情感的交流。我感觉残雪希望通过对爱的追求和对爱的书写,走出一种精神困境,进入到灵魂的深处。非常有意思的是,她的处理是去习得这种爱的能力。

△ 残雪与她在工厂使用的机器
现在来看,《激情世界》这样的小说我们要复述《激情世界》的故事,也不是那么有难度了。我在想一个问题,残雪的创作变化,一方面是她对于先锋写作的坚持,另外一方面也是考虑到读者进入到这个故事的过程,残雪可能稍微降低了对读者的要求,读者可以经由他们个人的阅读体验进入到残雪的小说世界了。
03
在残雪的小说里
获得与世界重新沟通的方式
郭冰茹:我们一般阅读的时候,首先打动我们的可能是情节,或者人物形象,我想问安仪老师,您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进入残雪所建构起来的文学世界?
冯安仪:刚开始的时候当然很难,但这是应该做的,我觉得这是《激情世界》出版的重要性,这本书告诉我们要怎么做。书里的人都在努力地阅读,一起在读书会上发言,说心里话。书里有很多例子,比如“阅读真是个好伙计”,“书是人的伴侣”。我觉得残雪新的小说是教我们怎么阅读、怎么享受她的文学。比如书中的小桑固执地认为,如果作者不能让一本书的内容与日常生活交织,他就没必要读那本书了。
郭冰茹:庆祥,你曾细读过《山上的小屋》,从《山上的小屋》到《激情世界》《西双版纳的女神》《少年鼓手》,你觉得这几本书里的情节或人物或细节中,让你印象最深的地方是什么?
杨庆祥:中国当代写作已经被高度修辞化,它是言不及意的,这其实恰恰丧失了文学表达本身的力量。残雪的句子都比较短,她的人物出场也是说来就来,没有太多的铺垫,这其实是一种非常难得的直接性。我曾经给万玛才旦的《故事只讲了一半》写过一个推荐语,我说这种直接性是对中国当代写作过分修辞的一种反驳,这个可以用到残雪这里,残雪的写作,对于我们惯常的印象来说是颠覆的,我们总觉得先锋作家喜欢玩技巧、喜欢玩修辞,但她恰恰不是,她的写作恰恰是一种非常直接性的写作,她是对中国当代写作里那种虚假修辞的反驳。这是我感受比较深刻的点。
还有一点,我不觉得她有多少故事,即使有也是支离破碎的,而且这个故事如果严格按照戏剧或电视剧的情节要求,有很多不合逻辑的地方。但这没关系,重要的是她小说里内在的情绪变化。《山上的小屋》以及《黄泥街》系列,整个内在情绪是非常阴郁、非常紧张的,但是《激情世界》表现得特别放松,这是特别好的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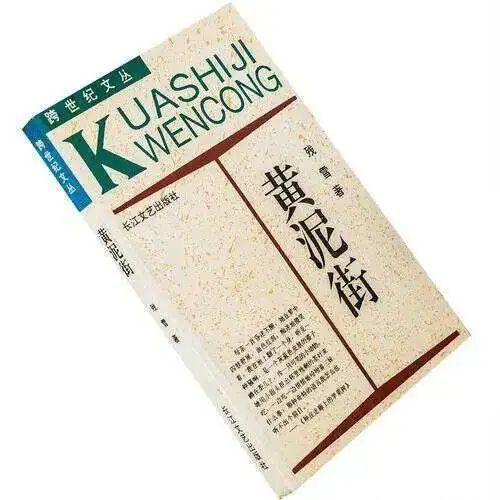
△《黄泥街》,长安文艺出版社 《跨世纪文丛》第四辑出版
一个先锋作家往往跟现实、跟写作之间保持愤怒的关系,这种愤怒有时候会损害作品本身的质地。而我在《激情世界》里面看到一种放松,她非常自由地把元小说的东西与生活的东西揉合在一起,而且来回穿梭,非常潇洒。
我觉得可以用这个词来表达,相对以前故意要搞实验,故意要装作很高深莫测的形象相比,我觉得她现在变得潇洒,变得轻松,变得自如了,所以这时候我们读她的小说也会有一种轻松感。
像《激情世界》这样的作品,你不需要从第一句往最后一句读,随便翻开其中几页都可以读,因为它也是一个文学评论,也是自己观念的表达,她也是一个元小说,关于阅读的小说,关于小说的小说。什么是好小说?我们通过小说能获得什么?获得爱,获得跟他人的理解,获得跟世界重新沟通的方式,在这里面她做的非常自如,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还有一点,一个作家,尤其中国当代作家,到了残雪这个年龄,很少会写爱情,尤其很少会去写青年人的爱情,因为很难把握,你不太了解这些青年人在想什么。但是残雪敢去写,她很自信,她认为爱是普遍的,阅读也是普遍的,不管是什么年龄的人都要经历这个,爱在本质上是有相通之处的,所以她能把青年人的爱写得非常鲜活,我觉得这是很了不起的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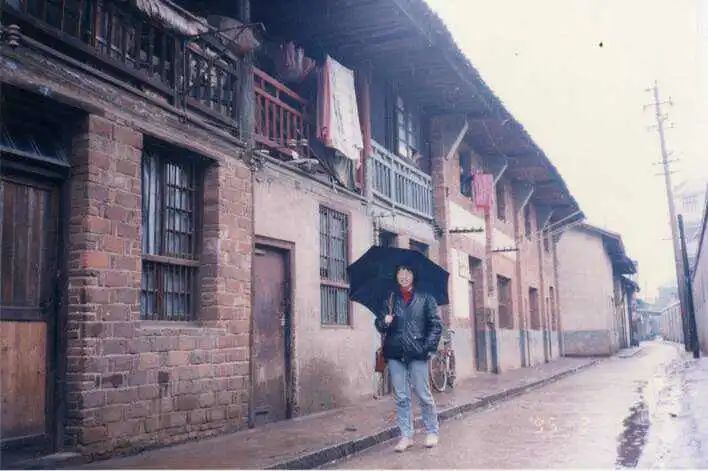
△ 残雪,1994年 / 摄影:残雪的日本译者 Kondo Naoko
刘长征:我特别喜欢一个短篇小说,名字我忘了,小说里有很多意象,一个人去高楼上班,住在一个很小的屋里,天空中一些发光的影像,有两个美少女,有一个地下花园,其实这些意象之间有一种必然性,你反复读好几遍会觉得它自然是这样的,比如天上的景象跟地下花园有一种神秘的关系,但不是你能用语言来叙述的。文学就是用感性构成的理性认识,这种高级的文学代表一种理性,但又不是概念的理性。
比如一些19世纪的作家讽刺资本社会,一个句子就要概括,大家就会觉得这是乏味的概念,但这个概念你可以写一个深度的文学。所以文学给人的并不是这个概念,而是通过品味这些意象带给你的感性反映,你会变成一个更敏锐的观察者,观察整个世界,观察你自己,观察宇宙本来的面貌。
这是残雪为什么写作那么放松的原因,就是她发现了这个过程,我们通过对崇高艺术的理想所达到的境界,无疑就是爱的境界。身体力行也是充满爱的,这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事实,这可能是残雪想传达给我们的。
,残雪createevent 这位中国作家,为什么在国外更受欢迎?相关:
写作是超脱,也是壮胆 | 9月新书,推荐这 14 本9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请查收本月新书推荐——如果你对女性写作感兴趣,本月书单既涵盖去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埃尔诺(本月有两位推荐人不约而同推荐了她的作品)新近在国内出版的两部作品——小说《羞耻》与对谈录《写作是一把刀》,又有直接探讨女性创作的“德博拉·利维女性成长三部曲”第一部《我不想知道的事》。如果你对更为广泛的女性主义话题感兴趣,上野千鹤子的新书《无薪主妇》与孔慧怡《五四婚姻》不容错过。上..
民间文艺走向新时代,有哪些变与不变?民间艺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具有久远的历史、广泛而丰富的内容与复杂深厚的社会关联性,二者相互交融、相互影响,是一个民族或地区文化传承中不可或缺的文化基因。李守白在开幕式上发言9月26日,第五届上海民间艺术成果展在上海市文联文艺会堂展厅开幕。此次展览的主题为“变与不变——走向新时代的民间文艺”,力图用创新的表达方式,展现当下传统文化在创新中求发展的可喜景象。展览内容包括长三角名家大师邀请展、优秀作品征..
无论做了多少家务,似乎总有更多在等着我“无论我做了多少,似乎总有更多在等着我。”这种感觉对很多女性来说再熟悉不过了——家里牙膏、卫生纸快用完了,阳台的衣服早就干了,只有母亲会注意到,这些举手之劳的家务,除了家中的女性之外,好像大多数人不知道主动去做。而且,大多数家庭成员把做家务视为“帮妈妈的忙”,而不是做该做的事……长久以来,男性和女性都习惯相信这种迷思,认为女性先天就是比较擅长这类事情。而事实上,没有人先天更擅长什么。然而,其实日..
上了班以后,才知今生唯爱自由 | 重读陶渊明凡是不朽的文学作品,都是永远说不完的话题,每个时代都可以对它作出不同的解读,常读常新。陶渊明的作品至少有两篇,一是《桃花源记》,一是《归去来兮辞》,是永远不能道尽的。如果说,《桃花源记》是渊明社会政治理想的结晶,那么,《归去来兮辞》则是渊明道德人格实践的记录。桃花源旋开旋闭,幽眇难寻,真所谓“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归去来兮辞》由仕而隐,乐天知命,一切实实在在,读之即在目前。前者系念..
凡他触摸的东西,都会变成诗歌 | 聂鲁达逝世50周年巴勃罗·聂鲁达1904年7月12日—1973年9月23日马尔克斯说:“巴勃罗·聂鲁达是二十世纪所有语种中最伟大的诗人……凡他触摸的东西,都会变成诗歌。”聂鲁达1904年生于智利帕拉尔,19岁出版第一部诗集,20岁享誉全国,被誉为“人民的诗人”。1971年,聂鲁达获诺贝尔文学奖。于他自己而言,固然任何一个作家都想获诺奖,但媒体的叨扰和多年陪跑带来的疲惫却也让人烦恼。他戏称,诺奖获奖者的庆典和外省小城的小学发奖仪式相似。或许..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愿意去爱?“好想恋爱啊!”虽然年轻人嘴上这么喊着,但肉眼可见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愿意去爱了。嗑CP、追星、找搭子……他们似乎更倾向于服用”爱情代餐“。既然动动手、花花钱就能获得极为丰富的情感体验,何必要花功夫经营感情?而在山田昌宏看来,这不单单是一种选择,更是一种困境。下文摘编自山田昌宏《社会为什么对年轻人冷酷无情》,本文经出版社授权推送,小标题为编者拟。01找不到恋爱对象的年轻人据说“逆向巧克力”蔚然..
影响费翔一生的作家安·兰德,曾被误解为庸俗价值观的捍卫者“在一般的采访中我提到安·兰德,没有人会认得,只有你会认得,我特别高兴。”在《十三邀》对费翔访谈中,初代偶像费翔和许知远谈到对他影响最深的一位作家,他说:“安·兰德是一个蛮有争议的作家,我看了她所有的书,不止一遍。”美国作家安·兰德曾写下《源泉》《阿特拉斯耸耸肩》等数本畅销的小说,她的哲学和小说里提倡理性与个人主义,认为理想社会应是以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社会。在节目中,费翔讲到安·兰德对极端个人主义..
最高炒到3600元!新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品一书难求瑞典文学院10月5日宣布,将2023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挪威作家约恩·福瑟。随后,他的作品在中国“身价大涨”,许多读者表示一书难求。据当当网平台显示:诺奖公布后,约恩·福瑟的获奖作品《有人将至》搜索登上热搜榜第三,该书目前已进入预售状态。《有人将至》登上当当网热搜榜第三线上告罄,线下书店难买到对中国读者来说,约恩·福瑟是一个相对比较陌生的名字。上海译文出版社曾出版约恩·福瑟的戏剧作品选《有人将至》《秋之..
为什么小王子居住的行星那么小?小王子居住的行星为什么那么小?安部公房笔下的箱男为什么住在一个箱子里面?卡夫卡《审判》中的城市为什么像是一个迷宫?……这些看上去丝毫不会引起我们注意的细节,甚至毫不相关的几篇小说,在著名建筑师张永和笔下,却有了另一种视角,他试图分析那些经典文本中的建筑设计,从文本中为自己的建筑设计找寻灵感——“请不要认为我企图得出(某些)文学家等于建筑师的结论。奥布莱恩不是建筑师。卡夫卡也不是。而是我相信他们的..
新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疫情放大了性别不平等前几日,202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出,授予美国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以表彰她“增进了我们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结果的理解”。作为经济史学家与劳工经济学家,劳迪娅·戈尔丁40多年来的研究话题广泛,包括移民、收入不平等、科技变革等等,不过其中最为知名的,还是她在女性劳动方面的研究。其代表作之一《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的百年旅程》就是对女性劳动市场长达10年的深入研究之作。戈尔丁将20世纪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