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辛
澎湃新闻:《婚殇》《恋殇》关注的都是新上海人,你对于他们的境遇是如何把握的?
叶辛:我当知青的时候,上海的人口大约在1000万人,我1990年调回上海的时候,是1400万人,现在33年又过去了,上海的人口是2500万人。这些人从哪里来?根据统计,其中有近1000万都是新上海人,而且主要是年轻人,无论是大学毕业,退伍复员,还是来上海工作,所有这些年轻人都有一个融入上海的问题。我之所以关注到他们,是因为我自己有知青的经历,从上海到贵州的偏远山乡,当时也面对融入农村社会的问题。当然,这和新上海人所面对的境况不一样,但融入一个地方都是一个过程,体现在习惯、心理、生活方式、为人处世方方面面。
我关注这些年轻人在上海的生活,尤其是年轻女孩怎样融入上海,这和我在平时生活里的观察有关。比如我在单位上班的时候,我会注意到其他城市来的女孩,在食堂打菜时会挑选什么,或者是我兼任上海大学文学院院长的时候,听外地来的姑娘说话,大一的时候她们往往会说在上海生活不习惯,读了4年就要回去,但是过了半年,她们就不这么说了。有了这些观察,像《恋殇》的女主人公曾西亚的名字就慢慢从我脑子里浮现出来了。我观察到,来上海的年轻女孩大多是出生在县城或者内地的中型城市,读过大学,曾西亚就是这样,我有意地没有交代她具体来自哪里,“小城”只是一个概念,而来自小城的年轻人都要经历融入上海的过程。
澎湃新闻:从《婚殇》到《恋殇》都是从女性视角出发,这个视角是怎样形成的?
叶辛:我没有正式地采访过这些年轻女孩,有时候在饭馆里遇到比较熟悉的服务员,或是在电梯里碰到邻居,会顺口问上几句,主要是从她们的言谈举止中揣摩她们的心理,想象她们会过怎样的生活。比如我住的楼里有很多租房子的年轻人,我在电梯里经常遇到他们,也就熟了,有些人租进来半年一年,就搬走了,说两个人结婚,在外面买了自己的两室一厅了,我就会想她搬进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现在是什么样,这条“命运线”就慢慢出来了。观察和想象得多了,构思就慢慢地形成了。之前有人说,我写的这些女性都很善良,人都很好,是为什么?我觉得是因为这些人物都是从我的生活当中塑造出来的,我不希望她们过得不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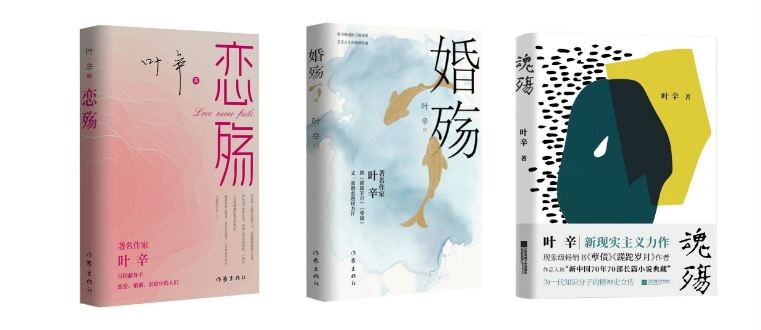
“殇”三部曲
澎湃新闻:你在《恋殇》后记中写到去贵州的山里写作,书中也有人物的背景是在云贵地区,云贵地区对你的写作来说意味着什么?
叶辛:贵州对我来说很重要。1969年3月,我19岁的时候到了贵州,快30岁时调到了贵州省作家协会,在山乡里待了10年的时间。我在生产队里和农民一起劳动煮饭,那段日子让我思考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思考了知青的命运,才会有我那些知青小说。
我在贵州的生活快结束的时候,又遭逢了农村的变革,从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演变到今天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如果你仔细看中国当代文学史,你会发现在1980年以前,中国的农村都以人民公社为主,1980年代中期开始,再看农村题材的作品,又回归到了原来中国农村农民自己种地的日子,这中间经过了复杂和阵痛的演变,我恰好都经历了,我的长篇小说《巨澜》写的就是这个过程。
澎湃新闻:之前你主要以知青文学而为大家所知,这次的新作以婚恋为主题,和知青文学有什么联系吗?
叶辛:我写了一辈子的小说,也想要有所改变。尽管我之前也写过都市题材的小说,写过省城里的风流轶事,但是这些其他题材的作品好像都被知青文学给掩盖了,人家一讲到我,就是《孽债》《蹉跎岁月》这些知青故事。我今年74岁,还是有写作的欲望。我觉得当代生活里最打动人心的就是感情、婚丧这些主题。我在当全国人大代表的时候,参与过《婚姻法》具体实施条例的修订,在落实的过程中,我要参与婚姻介绍和婚恋纠纷的调研,接触面广了,也就开始关注这个题材,婚恋是任何社会都要面对的话题,我想要从中捕捉这种时代性。
澎湃新闻:在今天,婚姻对于女性来说并非是必选项,你是如何看待独身女性的话题的?
叶辛:我在很久之前就开始关注这个话题。20多年前我去日本访问交流的时候,和日本作家交谈,当时他们就和我说,日本社会开始崇尚独身主义,男人喜欢自由自在,有体面的工作,下班以后和同事们去喝酒,日本的女性也不相信这些男性,大家都不想结婚。20多年前他们和我说这些的时候,我印象里中国社会对比之下还很传统,但到了今天,不婚不恋的现象在中国也很普遍。在我们的社会转型过程里,很多家长虽然还延续着传统婚姻的价值观,但是子女这一代已经不再传统,不愿意将就。
,excel乱码修复 专访作家叶辛:观察和想象年轻人的生活相关:
丰子恺译《旅宿》特装版:随夏目漱石走进山林最近,丰子恺翻译的夏目漱石的代表作《旅宿》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这是丰子恺翻译出版《旅宿》65周年全新纪念版。《旅宿》既可以看作是一本小说,也可以看作是游记散文。书中描写的是一位画家为了摆脱俗世的羁绊,背着画箱来到深山,一路沉醉于旖旎的春光和秀丽的风景。到达落脚的旅宿后,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了当地人的生活,形形色色的人物命运和各种离奇的故事让画家在“非人情”的世界流连忘返。奇妙的故事情节中充满了夏..
残雪这位中国作家,为什么在国外更受欢迎?近两年诺奖颁奖前后,残雪的名字就会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之中。今年尤其如此,她的长篇小说《新世纪爱情故事》今年在瑞典出版,译者正是当年翻译莫言作品的那位,出版后引起瑞典各大报刊媒体的讨论。诺奖结果公布前的几个小时,残雪高居博彩公司赔率榜第一名。然而,一旦获奖者不是她,她的名字便再次在国内消身匿迹。残雪是谁?如果不是因为诺奖,知道她的人并不多,读过她作品的人更是少之又少,这样一位被认为是最有希望得诺奖的..
“五月的玫瑰” 香港国际诗歌之夜2023,与北岛、贝列西共赴诗的国度深秋时节,诗意生长。10月15日-11月6日,由诗人北岛发起、创办的香港诗歌节基金会,将在北京、秦皇岛、上海、杭州、中国香港等地举办“五月的玫瑰” ——香港国际诗歌之夜2023系列活动。10月21日-22日,部分活动将在秦皇岛·阿那亚开展,以朗诵、舞蹈、音乐、对谈等多种形式,对话阿根廷当代国宝级诗人迪亚娜·贝列西(Diana Bellessi),邀请所有爱诗者的参与。本次活动由唐小兵策划。“请不要畏怯于诗歌,她如人类心灵一般深..
诺奖没有颁给残雪,而是给了这位“21世纪的贝克特”瑞典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10月5日13:00(北京时间19:00),瑞典学院将202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挪威当代著名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约恩·福瑟:“因其创新的戏剧和散文为不可言喻的事物发出声音。”(“for his innovative plays and prose which give voice to the unsayable.”)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官方网站,给出了更多关于约恩·福瑟的补充:“他用挪威尼诺斯克语写成的巨著涵盖多种体裁,包括丰富的戏剧、小说、诗..
写作是超脱,也是壮胆 | 9月新书,推荐这 14 本9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请查收本月新书推荐——如果你对女性写作感兴趣,本月书单既涵盖去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埃尔诺(本月有两位推荐人不约而同推荐了她的作品)新近在国内出版的两部作品——小说《羞耻》与对谈录《写作是一把刀》,又有直接探讨女性创作的“德博拉·利维女性成长三部曲”第一部《我不想知道的事》。如果你对更为广泛的女性主义话题感兴趣,上野千鹤子的新书《无薪主妇》与孔慧怡《五四婚姻》不容错过。上..
民间文艺走向新时代,有哪些变与不变?民间艺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具有久远的历史、广泛而丰富的内容与复杂深厚的社会关联性,二者相互交融、相互影响,是一个民族或地区文化传承中不可或缺的文化基因。李守白在开幕式上发言9月26日,第五届上海民间艺术成果展在上海市文联文艺会堂展厅开幕。此次展览的主题为“变与不变——走向新时代的民间文艺”,力图用创新的表达方式,展现当下传统文化在创新中求发展的可喜景象。展览内容包括长三角名家大师邀请展、优秀作品征..
无论做了多少家务,似乎总有更多在等着我“无论我做了多少,似乎总有更多在等着我。”这种感觉对很多女性来说再熟悉不过了——家里牙膏、卫生纸快用完了,阳台的衣服早就干了,只有母亲会注意到,这些举手之劳的家务,除了家中的女性之外,好像大多数人不知道主动去做。而且,大多数家庭成员把做家务视为“帮妈妈的忙”,而不是做该做的事……长久以来,男性和女性都习惯相信这种迷思,认为女性先天就是比较擅长这类事情。而事实上,没有人先天更擅长什么。然而,其实日..
穿越极寒之地,她是“死亡公路”上唯一的女卡车司机“我(埃米)是一名女作家,也是沉默的家暴受害者。她(乔伊)是一名卡车司机,在美国最危险的公路上跑运输。”在某次被家暴后,埃米决定“出逃”,前往阿拉斯加,与乔伊见面。两位女性一起穿越666千米的致命冰路,在属于自己的车里,她们无须解释与证明什么,也不用再寻求他人的肯定。在道尔顿公路,在北极荒野的狼群与驯鹿前,在乔伊的大卡车上,两位女性互相倾诉自己的经历和故事。埃米开始明白,她所钦佩的乔伊的勇气和韧性..
上了班以后,才知今生唯爱自由 | 重读陶渊明凡是不朽的文学作品,都是永远说不完的话题,每个时代都可以对它作出不同的解读,常读常新。陶渊明的作品至少有两篇,一是《桃花源记》,一是《归去来兮辞》,是永远不能道尽的。如果说,《桃花源记》是渊明社会政治理想的结晶,那么,《归去来兮辞》则是渊明道德人格实践的记录。桃花源旋开旋闭,幽眇难寻,真所谓“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归去来兮辞》由仕而隐,乐天知命,一切实实在在,读之即在目前。前者系念..
十九世纪的妇科男医生波齐:没有空窗期,每次都很真诚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是个地道的法国迷,对这个国家的种种如数家珍,奉福楼拜为文学偶像,曾被评价为“最具法国味的英国作家”。据《巴黎评论》的记者写,他家图书室的墙上,挂着一张乔治·桑中年时的绝佳照片,是纳达尔于1862年拍摄的,还有福楼拜一封短信的原件。尽管如此,在邂逅萨金特这幅《在家中的波齐医生》之前,他也从未在19世纪的法国著作中见过这位塞缪尔·波齐医生。画中人的猩红色长袍实在是很精美,它很长,从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