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的1962年3月20日,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C. Wright Mills)逝世,年仅46岁。在他逝世60周年之际,我们重读他影响范围最广的经典之作《社会学的想象力》,并以此反思社会科学的想象力。我们专访了陈映芳(社会学)、任剑涛(政治学)和刘海龙(传播学)等三位学者。本篇为对传播学者刘海龙的专访。
让我们首先从眼下的一个现象说起。
2021年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初试成绩近日公布,在考研越来越“卷”的今天,传播学因其几乎最高的分数线成为放榜当天考生们热议的焦点。作为当下中国最“火”的人文社科专业,传播学吸引着无数学子报考,但一派繁荣的背后,持续的学科焦虑却始终难以散去。依照传播学者罗杰斯在《传播学史》中的说法,现代的传播学学科化始于20世纪的美国(尽管这一叙事遭受过很多质疑)。学者威尔伯·施拉姆总结的传播学科“四大奠基人”如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卡尔·霍夫兰等大多来自心理学、政治学等多学科。这使得即使时至今日,“传播学有何独创的理论?”依然是这一历史短暂的学科常常遭遇的质疑。
不过,这种学科的“主体性焦虑”却也意味着学科想象力的开放性,这给予了传播学更多可能的发展路径。美国主流传播学将学科的重心聚焦于研究人类社会的信息传递活动,这也是现在公众从字面上对这一学科的理解。不过,确立学科边界虽有助于一门新兴学科的建制化,但也严重窄化了学科的研究范围。在《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一书中,学者刘海龙较早地对其进行了批判。在如今的中国传播学界,“打破学科壁垒”的声音早已不陌生,媒介环境学、传播政治经济学等多个更富跨学科色彩的领域正蓬勃发展。
正如米尔斯所写,社会学想象力的培养,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研究者不拘泥于“根据学院系科来确立自己的专门化研究”。只是,随着跨学科日渐成为趋势,新的焦虑也在浮现。可能很多传播学的学生都在自己的论文选题时遭遇一个常见的质疑:“你研究的话题是否是一个‘传播学’的问题”。一方面努力强调自己跨学科的特征,另一方面又极度在意学科边界,传播学面临的这种悖论一定程度上可成为我们思考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过程的典例。
刘海龙的观点是:传播学当然有其独特的视角,另一方面,也完全无需过度担忧所谓的“学科主体性”问题。在一个媒介技术飞速发展的社会中,我们需要更新既有的对人类传播现象的理解,认识到传播问题远不仅仅只是信息传递的效率问题,它还是“身体”、物流乃至“病毒”的问题。我们只有充分挖掘全新的看待“传播”与“媒介”的角度,才能赋予传播学持续前行的活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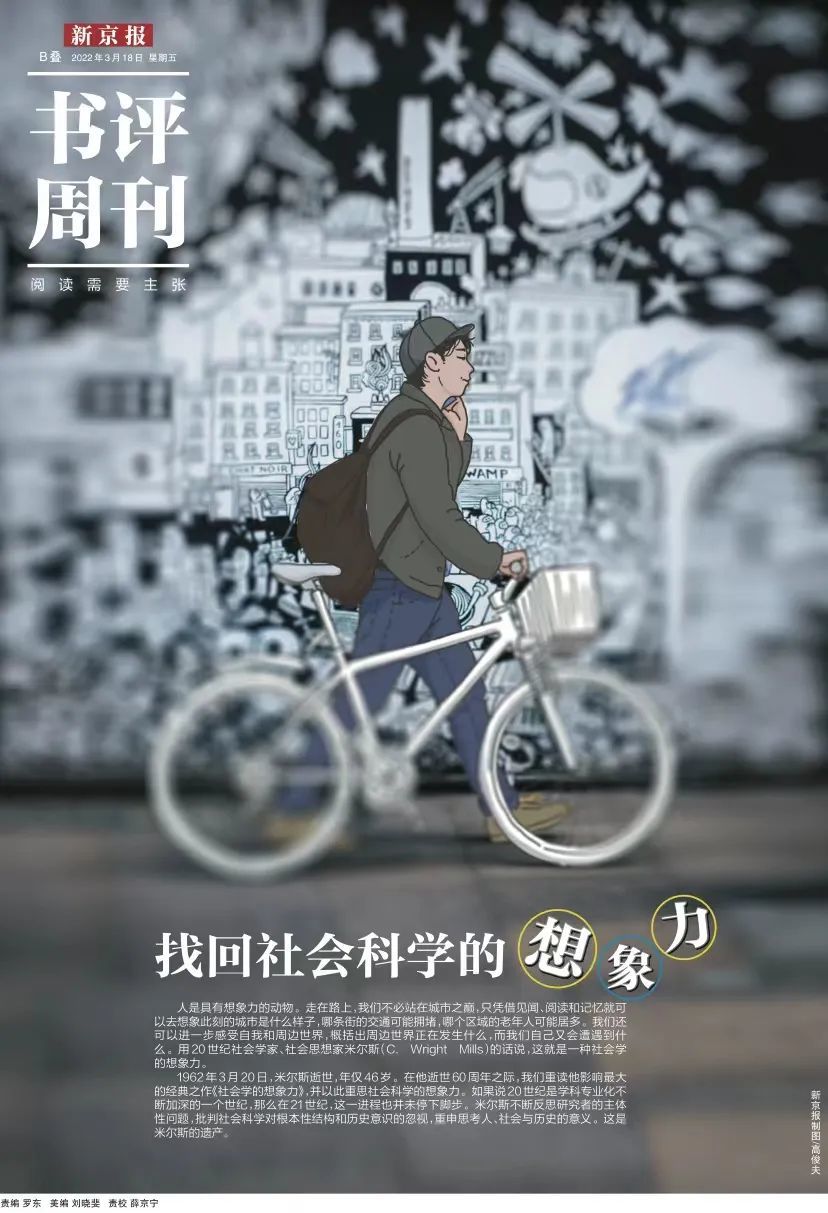
本文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3月18日专题《找回社会科学的想象力》的B05。

采写|刘亚光

刘海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重访灰色地带》《宣传》等。译有《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等。

米尔斯与早期传播学的分歧
新京报: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他曾批评过传播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拉扎斯菲尔德,他们也曾经合作开展研究,不过在进行《人际影响》的调查时,二人的思路产生了分歧。我们如何理解米尔斯和传播学之间的联系?
刘海龙: 米尔斯早期从事了很多传播学的研究,《社会学的想象力》里不止批评了拉扎斯菲尔德,还提到了斯托弗 (Samuel Stouffer) 、多德 (Stuart Dobb) 等,都是早期传播和宣传研究的重要人物。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和拉扎斯菲尔德一起在迪凯特做意见领袖研究,后来的作品中,包括《权力精英》等,也非常关注媒体对社会的作用。

米尔斯(C. Wright Mills),美国20世纪社会学家,生于1916年8月28日,卒于1962年3月20日。曾在威斯康星大学师从H.格斯和H.贝克尔,1941年获博士学位。生前长期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其作品《社会学的想象力》是社会科学领域引用率最高的书之一。
他前后期的这些研究也有关联。做意见领袖研究的时候,一开始所有的数据都是米尔斯带着学生去收集,做得很辛苦,这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发问卷那种抽样调查,而是挨个去访谈,比如问一个家庭主妇,在哪些议题上受到了别人的影响或影响过别人,然后再滚雪球式地继续找到这个影响者或被影响者。这里面其实就能看出他研究上的追求,并不是想浮在表面上去简单搜集数据,而是想亲身接触具体的人,在人际网络中把握实在的关系。后来到了《权力精英》,他把人际影响的问题放到一个更大的框架里,即精英借助媒体如何对大众进行操控,他也点出了这种操控对非理性舆论形成的作用,这个问题在今天自媒体时代和民粹主义时代更明显。
米尔斯对权力的批判立场,和当时去政治化的主流传播学很不相同,执行项目的米尔斯和主持项目的拉扎斯菲尔德因为意见分歧反目成仇,终生不在同一个场合共同出现。《人际影响》后来在米尔斯退出后由拉扎斯菲尔德、卡茨重新分析他留下的数据,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书。

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F.Lazarsfeld,1901-1976),社会学家、传播学家。他1901年2月13日生于奥地利维也纳,1925年毕业于维也纳大学,曾获数学博士学位,后来对社会心理学和传播研究产生兴趣。著有《社会科学中的数学思想》《社会研究的语言》等。
托德·吉特林后来在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媒介社会学》 (Media Sociology) 中对其提出了批判,其中特别提到了研究的资方背景。这个研究的赞助方是一个读者定位为中下阶层妇女的杂志。米尔斯通过研究试图说明:人际影响是一种从上到下流动的垂直控制,而非水平流动。这个结论不利于杂志及广告商。因为如果影响是垂直流动,那么广告只需要投放到精英杂志,而不用在各个阶层推广。此外,研究设计的问题也非常微妙,当时设计的4个研究领域中,前三个分别是日用品购买、时尚、电影,最后一个是公共事务 (即政治) 。结论是在最后一个问题上人际影响的垂直流动是比较明显的,前三个都是水平流动,因此人际影响主要是水平流动的。但其实前三个按照分类都可以归结到“消费”这一类,而消费,其实归结下来还是很受大众媒体营销这类垂直流动意见的影响。
新京报:米尔斯提出的这种理论取向,和美国传播学初创时期的迥异。施拉姆所奠定的传播学创始人神话,虽然使得学科走向建制化,但也因此窄化了传播学的学术想象力。米尔斯所批评的“抽象经验主义”,很多都适用于对传播学的批评。
刘海龙: 吉特林的文章里就提到了这方面的问题。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调查混淆了两种影响,一是结构性的、自上而下的权力的影响,一种是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影响,人际关系和权力本质上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不能简单比较。这个其实也反映出很多学者对权力、结构的忽视,误以为通过人际的影响就能完成很多大的改变。缺失了这种观照,其实像拉扎斯菲尔德这类实证研究,看似是经验性的,但其实只是一种“抽象的经验”,摸不到社会真实的脉络。
不过米尔斯更多时候还是一个理论上的“孤勇者”,因为当时拉扎斯菲尔德他们的研究是依托在一个产业化的模式上,市场调查、民意测验是一个很热门的产业。整个传播研究其实比较像是在办“企业”,用一种很标准化的、项目制的方式做研究。到了米尔斯之后,这基本上也成为了美国传播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咨询式研究的风格,并且近年来也被国内大力提倡,米尔斯也批判了这种“科层制”的研究趋势,这其实和强调个人关怀、具体经验的人文社科研究是相悖的。所以其实米尔斯还是可以往前走一步,这种弊病背后有深刻的社会结构因素,并非是靠个体“想象力”的提高能解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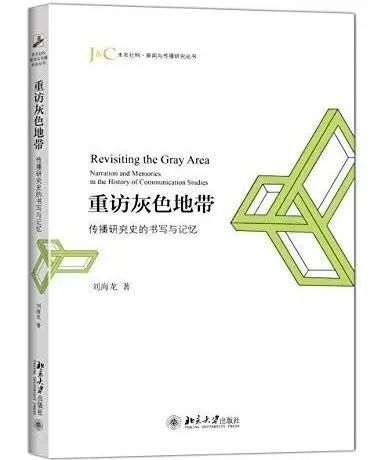
《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刘海龙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7月。

传播学的身份问题
新京报:说回到传播学本身。前两年清华大学拟取消新闻传播专业时,社会又开始讨论“新闻是否无学”的问题,其实学科焦虑的问题,传播学也存在。作为一个非常典型的交叉学科,传播学经常面临的质疑就是没有自己的独立理论,研究的问题都是在借用别的学科的视角。在你看来,什么是属于“传播”和“媒介”的独特视角?
刘海龙: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媒介/传播研究并非一个独立的学科,而是一个领域。其实传播/媒介是否构成一个独立的视角,本身确实一直有争议。我觉得如果从传播学的起源来看,“权力”或影响力可能是传播学的一个切入问题的重点,最开始传播研究处理的就是包括政府的宣传竞选、政治传播、说服中的修辞等问题。
此外就是这几年大家讨论得比较多的媒介理论,媒介也是传播学引入的重要观念。那么什么是“媒介”的独特视角,我觉得可以归结为一个“第三性”。我们知道,西方哲学传统从古希腊开始更多强调的是“二元性”,比如主客二分、笛卡尔身心二元对立之类的。海德格尔想突破物和人的二元对立,认为其实是一元的,人拿起锤子就知道怎么用,是一种“上手性”。但这里面依旧忽略了一个“中介”的问题:拿起工具之后开始用,这个过程并非是自然的,里面至少有“手”的中介作用。“手”或者说“身体”,其实就是一个哲学意义上的媒介。这个例子想说明的是,媒介并非一个实体,而是一种视角,让我们意识到很多二元对立中间有一个“中介”过渡。这是一种基础观念上的变革,将影响我们重新看待人与世界的关系。现在大家讨论得比较多的媒介化或者中介化理论,就是把媒介重新引入对社会问题的讨论之中。
我近些年特别关注“身体”问题,其实也是受到这种视角的启发。看我们今天最新的技术,包括VR、元宇宙等等,其实都和身体这个媒介非常相关。过去我们经常认为自己可以“直接”认知世界,和与世界打交道,身体的作用一直隐而不显,现在我们面临一个抽空身体的交流状态,突然一下,你和世界的关系、你对世界的基本认知就会出现颠覆性的变化。这在以往的传播研究很少被关注,但其实是传播研究最根本的一些问题。在这些问题上,一些媒介理论家提出的新观点能够给我们打开想象力的边界,比如约翰·彼得斯在《奇云》中提出新媒介,其实是让我们回到大众传播媒介之前媒介的基本功能,而不仅是关注传递信息和符号。
![《奇云》,[美]约翰·杜海姆·彼得斯 著,邓建国 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12月。](https://x0.ifengimg.com/ucms/2022_13/6354ED3FBCD75CA3F92652CD34609FEB9722201D_size58_w400_h562.jpg)
《奇云》,[美]约翰·杜海姆·彼得斯 著,邓建国 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12月。
新京报:传播学经常被称为“十字路口”,各路学科的思想资源都在此汇集。不过这里面有一个悖论式的问题,一方面,传播学者经常强调要注重跨学科的视野,另一方面,这个学科似乎一直又都有“主体性”的焦虑,很希望证明自己的高度学科化。你会怎么看这个问题?
刘海龙: 就像刚刚我说的,我觉得传播学是有自己独特视角的,比如媒介的视角,但我们也不能说这种视角有多么独一无二。比如我们现在研究物流系统的问题,做管理学的可能更多会把重点放在物流的效率上,但我们可能会关心其中的技术基础设施,关心其中对劳动者的控制问题。
其实我一直认为学科主体性焦虑是一个很虚无的东西,我们只要面向真问题,用独特的视角去解决它,给出知识贡献就够了。而且有一点我们需要注意,“主体性”经常意味着“独立”,但传播学中的很多核心的概念本身就是不独立的,比如媒介就意味着“连接”,是他律的,我们不可能忽视连接两端的那个东西去纯粹地谈论媒介。所以我一直说传播学最严格的叫法应该是媒介社会学或者是传播社会学,它一定不仅仅是传播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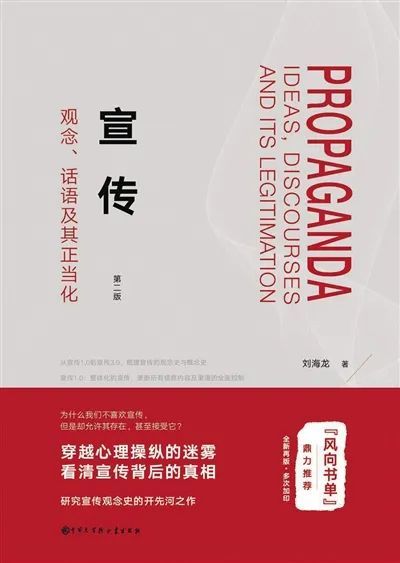
《宣传》(第二版),刘海龙 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0年1月。
我们也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越是缺乏“身份”的学科对学科身份越在意,反倒是一些早就不存在所谓学科合法性的学科,不会频繁地提这个说法。而这导致的一个结果,让传播学成为了中国形式上最学科化的社会科学。我把它称作一种“深度学科化”,我们在用各种形式不断地“筑墙”让自己显得很像一个学科,每年开社会科学当中最多的会,各种学科建制化的措施如火如荼地进行——当然也包括报考传播学变得越来越“卷”。但这更多还是一种形式上的“繁荣”,内在地来看,现在国内的传播研究在学术上还比较初级,甚至缺乏一个稳定的、有共识的判断研究“好坏”的标准。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焦虑也来自于时代的变化。传播学一开始很热的那些方向,比如舆情研究、各类效果研究,在新媒体的到来,乃至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崛起之后,能做出的新发现几乎乏善可陈。很简单的道理,以往我们做效果研究是希望通过抽样的数据来“推测”消费者的行为,现在的技术条件已经可以直接让你看到乃至预测这些行为了。所以传播学还是需要打破传统,去思考一些更根本的问题。这几年大家对“媒介”及其相关理论的关注也是做出的努力。

召唤传播学的想象力
新京报:除了身体问题,你还在疫情期间写过“病毒传播学”,这也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提法,但也难免让人有疑惑,觉得病毒更多是一个严格的免疫学问题,将其和传播联系会很牵强。你会怎么看传播学想象力的边界问题?
刘海龙: 我那篇文章其实主要还是想从传播学的角度为我们看待病毒提供一个不一样的视角,它可能并不完备,但这对我们从多方面看问题肯定是有价值的。每一个学科,每一个理论家,讲出的都不是绝对真理,也不能定义看待问题的角度只能有一种。我们会发现传统的传播学谈起传播、交流,不论是希望提高传播效率,还是改善人们的观念,都会认为“达成理解”是最终目的。
但是病毒成为一个让我们反思传播本质的一个很好的参照,因为在病毒这里,免疫系统“无法识别”,传播“失败”,才是一个最好的结果。这里面其实也扩展了我们对传播学可以谈论的对象的范围,比如“物”也可以被纳入进来。而且这个提法也并非天外飞仙,我们都熟知的传播学者罗杰斯在那本很有名的《创新的扩散》里也讲过病毒。它和新闻、杂交玉米种、政治观念、新产品的扩散都从属于更一般的传播概念。我有博士在写的“物流”,它们似乎并不是传播学的传统议题,但它们都很有价值。当我们的想象力打开,其实会发现传播是一个非常广义的概念,我们生活中有很多日常用语,使用的都是和传播学相关的词汇。
![《创新的扩散》(第五版),[美] E.M.罗杰斯 著, 唐兴通、郑常青、张延臣 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年1月。](https://x0.ifengimg.com/ucms/2022_13/6C87F16AF44BDA1D14CF5D5CC3727D5C561DA0DB_size65_w930_h1156.jpg)
《创新的扩散》(第五版),[美] E.M.罗杰斯 著, 唐兴通、郑常青、张延臣 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年1月。
新京报:关于激发社会学的想象力,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注重从本土经验生发出具体的理论,这也是米尔斯在批判“抽象经验主义”后提出的建议。作为肇始于西方的学问,传播学和其他很多学科一样也都经历过“本土化”的争论。你最近几年也在强调梳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传播”“媒介”等观念的重要性,它们和其在西方的内涵有不小的差异。可否大体谈谈?
刘海龙: 不止是传播学,其实任何一个学科的本土化都需要克服用自己的材料去套西方范式、理论的问题。目前这个工作可谓是任重道远,因为它对研究者的历史学、考古学等多学科的积累都有很高的要求。我概要地谈一些有意思的话题,中国和西方传播观念的一个很大的差异其实和宗教有关,在西方谈传播很难脱离宗教。而挖掘中国本土思想中的传播观念,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注意传播和“天”的联系。“天”一开始可能是自然化的,但后面会抽象发展成一个意识形态。其次就是传播的目的性,西方的传播 (communication) 观念一直非常强调“平等”、“独立”,但中国的传播更追求一种和谐、同一性。比如我们非常喜欢有关“水”的隐喻,因为水最终会汇集到一处。
用更有想象力的视角来看,中国古代也有很多有趣的“媒介”,比如卜筮、礼乐、祭祀、庙宇、旅行 (进京赶考) 、书写。书写的问题特别值得一提,我们能从中国人对书法的重视中看到,其实中国人关注媒介的意识比西方人还强一些,我们对做事的“中介”、“间接性”很在意,通过杨联陞所说的“媒介人物”与他人建立关系。就像书法的精髓并不在于你书写的内容,而在书写本身,那些线条与人的身体之间的节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书法本身也是一种“录像”,你看着书法的笔迹,甚至能想象出书写者身体运动的姿态,并“体会” (“体会”的本义就是通过身体领会) 其精神状态。书法本身就是一种媒介,是一种对活的身体姿态的记录。
新京报:米尔斯非常强调知识分子的公共介入,包括他在书里提到过“小册子”,认为这种传播形式非常适合连接大众与高深的学术圈。在让知识扩散、走向大众这方面,传播学者可能会更有体会。知识分子介入知识传播应该采用怎样的方式?
刘海龙: 首先,我们需要意识到让知识走向大众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其实也是意识到“观念”的社会影响。过去我们可能会觉得,尤其是人文社科思考出的那些东西,对社会并没有什么用,但正在发生的现实说明并非如此。比较典型的就是像罗萨的加速社会、韩炳哲的倦怠社会,这些观念逐步的流行,确实对大众重新看待工作、消费等有了一定影响,大家对“996”等现象的反思,很难说没有这种观念解放的作用。
不过需要承认的是,中国学术圈的“鄙视链”还是存在的,专业学者常常会觉得为大众写作是更低一等的事情。但其实大众写作做得好的学者其实也有不可替代的能力,比如知识转化能力。像哲学家韩炳哲,他可能也谈不上有多高的理论原创性,但是储备丰富,修辞精妙,并且能够指向现实问题,把知识整合得很漂亮。
正是因为大众写作非常指向现实问题——各种“痛点”,这里面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隐患就是这种写作有没有可能仅仅是为了迎合市场?米尔斯虽然谈研究应该解决个人的困惑,但是个人的困惑也非常有可能被商业等力量利用,现在比较典型的就是一些知识付费项目催生的知识焦虑。所以还是回到最开始我们讲到的“社会学想象力”,在知识传播这件事上,我们指向的不仅是个人的困惑,还应该连接到一定的结构性问题,要以一种对待结构性问题的“严肃”态度来传播知识。其中最重要的,也是我认为区分好的和不好的大众写作的一个标准,就是写作者是在为读者呈现事物的复杂性,而并不以真理的代言人自居。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采写:刘亚光;编辑:西西;校对:薛京宁、郭利。
,传布袁庚 学若何战胜学科身份焦炙?|专访刘海龙相关:
俄总统新闻秘书:俄出格军事步履正严酷按打算进行当地时间22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是一场“有着严肃目标的严肃行动”,没有人认为仅需要几天时间就能完成。俄要确保乌从“反俄中心”变为中立国家佩斯科夫说,特别军事行动正严格按计划进行。俄罗斯的主要目的是“解除乌克兰的军事能力”,这也正是俄军只攻击乌克兰军事目标、不打击民用目标的原因,俄罗斯需要确保乌克兰从一个“反俄中心”转变为一个..
美军F22战机冲出跑道 升降架未能打开机腹受损美空军F-22隐身战机再次遭遇飞行事故,因故障冲出跑道,机腹受损。据美国佛罗里达州当地媒体《每日新闻》3月22日报道,当地时间22日,美国空军埃格林空军基地的一架F-22隐身战斗机在降落时发生意外,飞行员状况良好,已被救治。从照片看,F-22战机降落时某个起落架能正常打开,战机冲出跑道,机腹受损。据报道,去年3月,埃格林空军基地的一架F-22战斗机降落时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故,前起落架出现故障,机头撞上跑道。F-22“猛禽”..
成婚纪念日那天,丈夫让妻子去孕育中心看病“谁能在纽约过得很好?”去美国留学前,凌岚的母亲忧心忡忡地问。那是90年代初。30多年后,凌岚将在美看到的社会新闻和道听途说的故事加工,凝结成了一部短篇小说集。小说主角,是与作者类似的美国新一代华裔移民。他们半途来到纽约,也将死在纽约。异国生活不是想象中的阳春白雪,而同样充满辛酸和不如意:小夫妻因两次流产感情渐生嫌隙,丈夫压抑着内心的“豹子”,两人奋力弥合关系。在小说的结尾,“豹子”还是跳了出来,肆..
诗人张枣 :拥有先天,不胜孤傲张枣是80年代最具天赋的诗人之一,年少成名的他和海子、顾城、北岛等人一起,构成了那个“文学热”时代中的精神象征。在非虚构作品集《众声》所收入的这篇《诗人张枣之死》中,作者郭玉洁以简洁而精准的文字,回顾了张枣作为诗人的生命历程,也写到了不为人熟知的“中年张枣”,展现了他热爱红尘与烟火、并不那么诗性,甚至令人失望的一面。随着“市场”的90年代取代了“文化”的80年代,诗人的黄金时代过去了,张枣选择了远居德..
汪曾祺笔下的14莳花:风和日暖,人在花中周作人在《北京的茶食》中曾写道:“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春日赏花,大概也称得上这种“无用的必要”。下文从汪曾祺散文集《草木有心,人间有情》中,摘选其笔下的14种“昆明的花”:茶花、樱花、夜来香、波斯菊……在他的笔下,不仅..
社会学需要更多关于“现代”的研究|专访陈映芳60年前的1962年3月20日,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C. Wright Mills)逝世,年仅46岁。在他逝世60周年之际,我们重读他影响范围最广的经典之作《社会学的想象力》,并以此反思社会科学的想象力。我们专访了陈映芳(社会学)、任剑涛(政治学)和刘海龙(传播学)等三位学者。本篇为对社会学者陈映芳的专访。人与社会的关系是米尔斯阐释“想象力”的基本内容之一。当个体陷于一团混沌的日常体验时,借用社会学的想象力可以探寻周边世..
古 代 女 装 大 佬 简 史“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古人对于美人的描写,总会引起无限遐想,然而历朝历代对于女性的美其实有着各不相同的标准——比如远古神话中的女神们,身上总是带有一些动物的特征,而《诗经》中的女性大多敢爱敢恨、美得健康而朴素,到了先秦时期是“楚王好细腰”这种对于“骨感身材”的过度追捧,而唐代是否真的“以胖为美”也未经证实。不过,对于美的追求并不仅限于女性,中国历史上,早已出现惊鸿一瞥的“女装大佬..
在小区里,狗的孤傲比人更深刻编辑推荐:今天大部分人生 活在城市空间里 ,而组成城市空间的基本单元,不是街道,不是高楼,是一个个的小区。 如果有人给小区“著书立说”,他会写些什么?历史学家通常借助史料的文字记录理清事件的逻辑关系,拼接出一幅过去的图像。 学者徐前进却认为,这些文字记录不足以完整展示过去真实的日常生活: 在古代,老熟人之间如何寒暄? 商贩与顾客如何相互照应? 他们遛狗吗? 这些生活片段转瞬即逝,因重复性极高而显..
兰波、巴黎公社和诗歌看够了城市的“喧嚣和色相”,诗人“出行远去”。1875年,兰波停止了“写作和歌唱”,先是在欧陆徒步旅行,然后又去爪哇,也到过亚丁湾,最后在非洲,在帝国主义的艳阳炽烤中,他做起了军火走私生意。1891年,兰波在马赛去世,没来得及回到他的家乡。撰文 | 王璞1法国诗歌史上的谜案据说,1871年,一位17岁的外省青年到过巴黎。他名叫阿蒂尔·兰波。2021年,当我们纪念巴黎公社150周年时,似乎忘记了巴黎公社和诗的关系。“如..
中国人最爱的英国作家,为什么是他?电影《面纱》剧照想要试图评价威廉·萨默塞特·毛姆先生,您可能需要一本辞典。这是位话题性与争议性满满,著作、八卦同时等身的文学巨匠。而想要找到个阅读他的理由则再容易不过,虽然此人长期被评论为“二流作家”,但其20部长篇小说、9部短篇小说集、3本游记、9本随笔集外加29部戏剧,委实皮薄馅大,可读性奇强。祖师奶奶张爱玲,还有加西亚·马尔克斯、伍尔芙、乔治·奥威尔、王朔、白先勇、村上春树等一众文坛宗师都对他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