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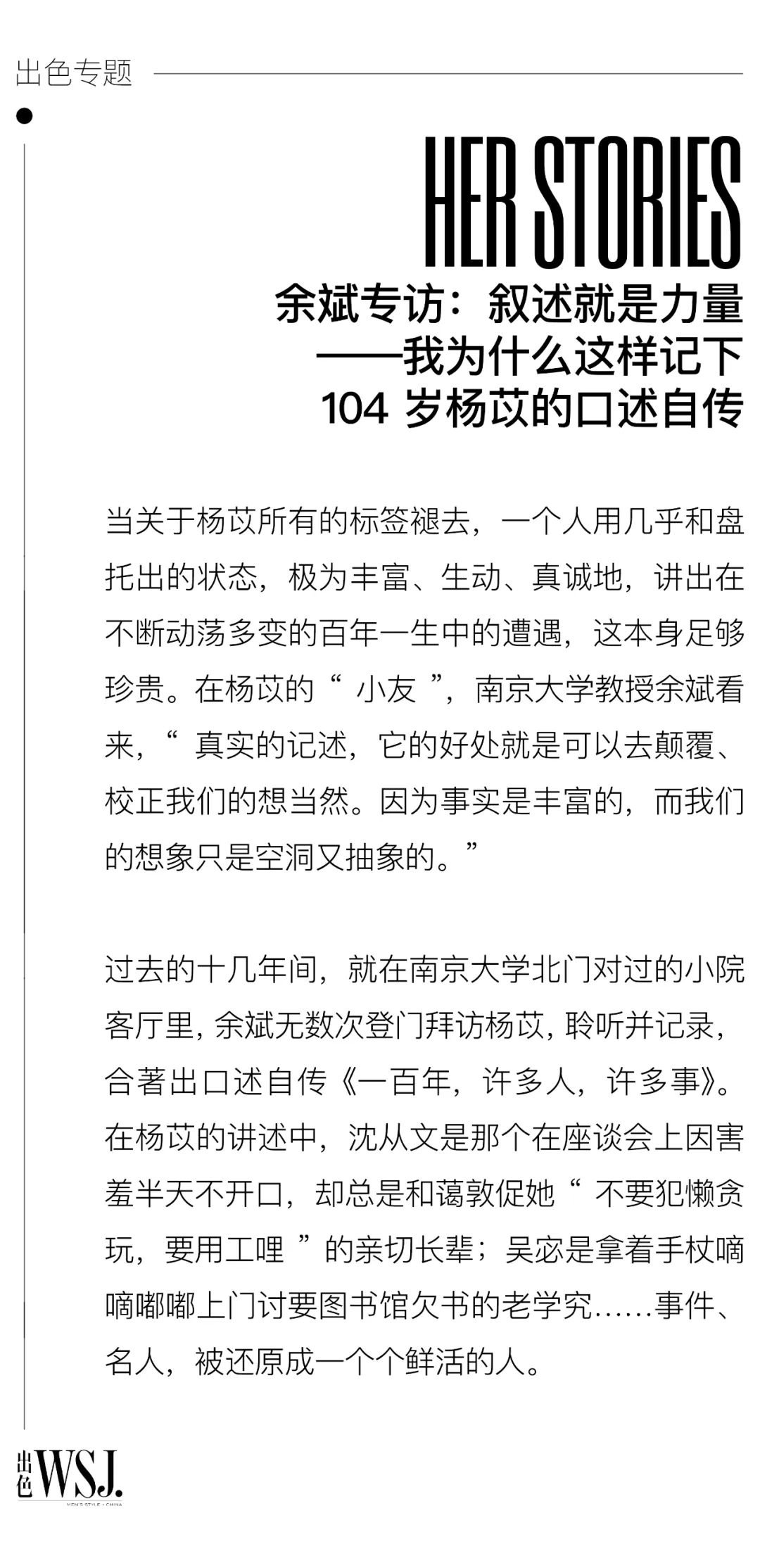

“在人们对她的描述中,有一个我觉得她是会接受的:祖母,经历了岁月沧桑、百年生活变幻的世纪老人。”杨苡的追思会和新书发布会上,余斌这么说道。
3 月 1 日,南京世界文学客厅举办了“在文字中与杨苡重逢:杨苡作品共读纪念”活动,既作为口述实录的发表活动,也是亲朋好友的一次追思会,子女赵苏和赵蘅都来到现场,长女赵苡也发来了视频。现场好像又回到那个热闹的客厅,耳畔依稀还有杨先生那句“活着就是胜利。”余斌说,“本来书的发布会和这个不好合一的,但我想杨先生是一个特别的人,可以用一种比较特别的方式。怎么让杨先生活着,就在书里活着吧。”

杨苡和余斌合著的口述自传《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赶在今年 1 月,她入院治疗的前几天顺利出版了。1 月 27 日晚,杨苡去世,享年 104 岁。
1919 年杨苡出生在一个天津的旧式大家族,同年,五四运动爆发。她的一生就好像在那一年写下预兆,有家族带来的教养与特权,也有新文化赋予的自由与革新。现在来介绍杨苡,可用的标签有很多,西南联大外文系学生、巴金的笔友、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和古典文学研究者杨敏如的妹妹、《呼啸山庄》译名的首创者……这些标签终显单薄,更多人认识到她,也许是关于西南联大的记录片《九零后》中那个谈笑风生,有着动人生命力的老太太。
就是在被拍摄的那间小屋里,这样的讲述发生过无数次。杨苡乐意同来访的熟人、朋友、记者絮絮叨叨地回忆她过往的故事和相遇过的人们。听故事的人里,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余斌上心了,决意要将她的口述编辑成书。

于是在过去的十几年间,就在南京大学北门对过的小院客厅里,余斌无数次登门拜访,聆听并记录下了两人的闲聊。在她的讲述中,沈从文是那个在座谈会上因害羞半天不开口,却总是和蔼敦促她“不要犯懒贪玩,要用工哩”的亲切长辈;吴宓是拿着手杖嘀嘀嘟嘟上门讨要图书馆欠书的老学究;蒋介石是到学校出席毕业典礼却遭遇冷场和讥笑的替校长。事件、名人,被还原成一个个鲜活的人,自发地活动在这份灵动的记忆之中。就连余斌自己,也褪去了职位头衔,成为不断发问、丰富细节的“小友”。
余斌在后记中写过这样一句,“长寿本身是一种资格”。惊人的记忆力让这份资格得以被生动见证,历史不再是只有定论的标准答案,而因为丰富的故事构筑起全新的生命。
二月底时,我们在南京拜访了余斌,在秦淮河边的下午,我们聊了聊一些记忆,一些“一面之词”。以下是余斌的口述。

杨先生住院以前的最后几天,一直在看这本书。她拿到书的时候,她有点激动,很开心,还说“怎么我就随便说说,就做成了这么厚的一本书。只是可惜母亲看不到了。”
对于过去的事情,杨先生不止对我一个人,对很多熟人她都会有讲述的冲动。尽管她说小时候内向,但我觉得她在初中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一个自己的话语场。我可以想象,如果她的那些闺蜜朋友还在,聚到一起的话,肯定是叽叽喳喳马上就热闹得不得了,大家抢着说话。

九十年代,杨苡与中西的同学们在天津相聚。
一般来说,面对一个年龄很大的人,说话总会注意点分寸,或是保持些距离。在她那里很容易就忘掉这些,可能自己都意识不到,这么大的年龄距离好像就跨过去了,自然地就可以比较放肆。我还记得有次去她家附近吃饭,喝了不少酒,突然想到一件什么事就上杨先生家去了。那时候赵先生(杨苡的丈夫赵瑞蕻)还在,我还只去过她家两三次,不算很熟,我也不是个自来熟的人。后来想想还是有点孟浪了,一口的酒气就去了,很不像话。
杨先生的天真、任性的性格一以贯之。她还有很多习惯,一直保持到老。她爱看电影,我们熟了以后,她动不动就打电话给我,“去看,《佳片有约》。”那是她特别喜欢的电视节目,常放老电影。杨先生打电话叫我看,然后没等我怎么反应,“啪”得就挂掉了,她急着去看了。但是她要跟你分享。
写信也是。但要有人给她写呀,像我们没有这样的习惯,有来也没去。比如她给我写信,我马上一个电话就打过去了。到最后还常常有事就写一个条,可我还是打电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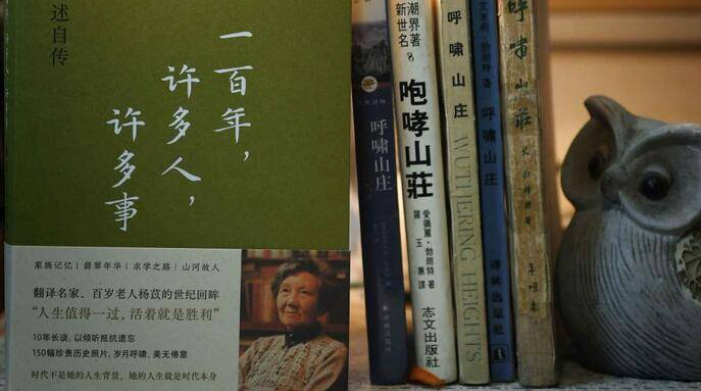
她还有看报的习惯。她母亲原来的文化程度很低,父亲就叫母亲一定要看报,母亲就此养成了看报的习惯。杨苡先生受母亲的影响,一直到最后也每天都看报,后来也会常常给我讲报纸上的事情。事实上我早就不看报了,她就会把报纸剪下来,哪天看到了我的文章还说要给我剪下来,或者叫人去复印保存。我说“杨先生不需要了,手机里都有,马上都能看到”。
晚年时,翻译她不太做了。她也从没说过自己早年就立志要做一个出色的翻译家。但她有时候还会琢磨,这个要翻成什么,那个翻得不对。翻译这件事她觉得很有趣,一直都是这样。
杨先生会写点散文随笔,她就给我看,说是“作为文学同行”提提意见,我想我怎么给长辈提意见,但我确实是有意见啊。后来还是提了。我说,“杨先生,用不着这么多惊叹号的”。她的感情特别丰沛,这也是有意思的地方。你看口述里杨先生没有那么多伤春悲秋,没有那么多色彩对吧?所以我说文章中的杨先生和口述时的杨先生是同一个人,但又不是完全重合的。

杨苡喜欢娃娃,家中收藏着许许多她喜欢的娃娃、摆件。
确定要做这本口述书之后,我更经常到杨先生家。从我家过去,骑车大概 15~20 分钟左右。没有什么固定的频率,我就是随时去随时出现。有时候自己开了门就进去。杨先生也不讲究这些。到了后来,我一走,杨先生还会问,那明天我们说什么呀?我就说说什么,但事实上第二天说的什么,也不一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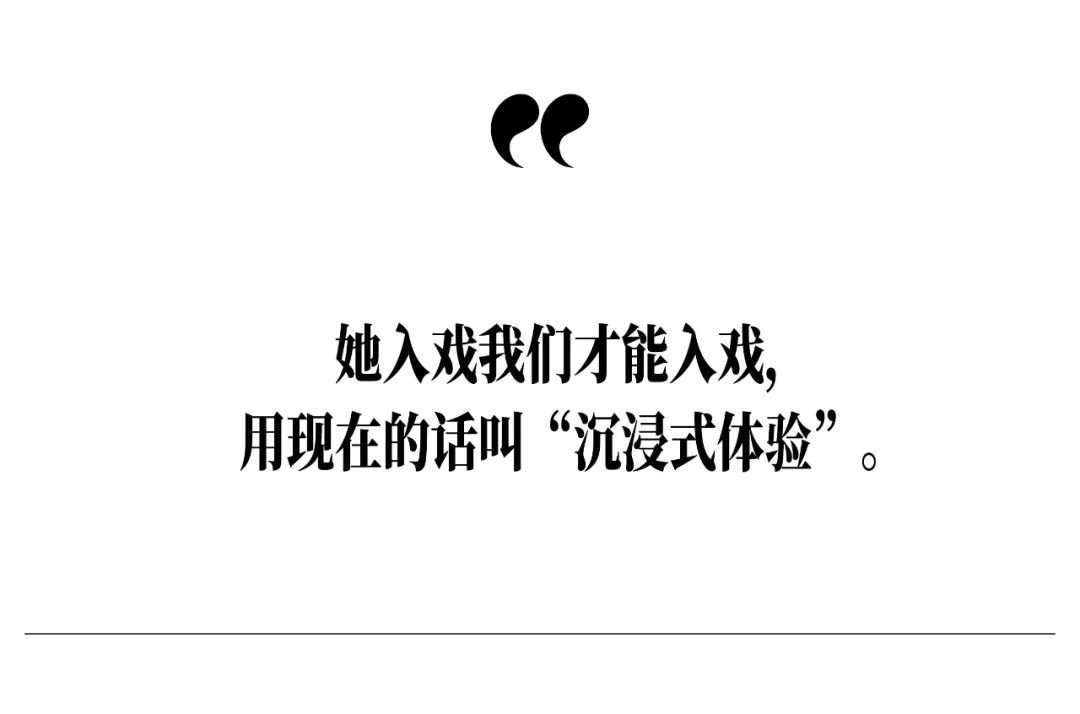
我们聊天的时候,话题总在不断地变化,时空也不断变化。因为是比较近的人,很多事情默认你是知道的,就不会有一个连贯的叙述。经常是随意讲讲,然后回溯的时候,都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讲到这里来的。有时候比如保姆来了喊“奶奶吃面包”“喝点牛奶”,她就烦躁,“又叫我吃又叫我吃”,然后一停顿马上开始讲到家里的事情。有时候又是哪个邻居来电话了,“烦死了,也叫我吃什么东西。”这个人我不知道,她就开始跟我讲这个人是谁,他们家在哪里。尽管我并不需要这些信息。
书里的很多细节都是我问出来的,比如我感兴趣他们从重庆是怎么坐船回来南京的?在船上怎么住?下雨了怎么办?这么一问,她就会告诉我在甲板上很多人用粉笔画一块,大量有意思的细节就是这么来的。我想到了就会问,而且一问她就马上想起来了,真是叫小叩小鸣,大叩大鸣。
她的记忆力太好了,给她一个刺激,她马上就有很生动的还原。对杨先生来说最好的状态就是成就她的“昔日重现”,进入一种纯粹的回忆,是她最惬意的,也是我们(读者)今天可能得到最多(故事)的方式。她入戏我们才能入戏,用现在的话叫“沉浸式体验”。
不夸张地说,我在书里记述到的很多东西,杨先生讲了十几二十遍是有的,比如讲大公主的一篇,可能是 10 次以上讲述的集合。每次讲述都不一样,我在听的时候也会有新的发问,哪怕只有新加了一个细节,我也要填补上去,有时可能文章都已经定稿了,她又同我讲起来。她反复讲,我反复听,仍有所得。

书里好像都没有写赵先生什么好话。我看到反馈的时候心想说坏了,赵先生要身败名裂了。我觉得人们对口述史应该有一个阅读的前提,就是我们知道它是有限的视角。比如面对同样的一件事情,赵先生的讲述就不会是这样,而这是杨先生的回忆,她可以有她的偏见,这就叫作“一面之词”,我默认读者都会有这个自觉,但现在似乎其实不是。
杨先生和赵先生的关系肯定有她讲述的那一面,我还打了一点折扣的,有一些吐槽得更狠。有些报道里说我是赵先生的学生,其实我不是(只是有一门公共课),老实说如果我是的话,可能打的折扣还要更多些。

杨苡、赵瑞蕻,抱着两人刚出生的大女儿赵苡。
书里面有提到过一个她和赵先生的温暖时刻。他们在云南跑警报,因为抱着小孩跑不远,就躲在楼梯肚子里,赵先生安慰她说:“不会有事的,你看我们小孩长得那么漂亮。”很传神的一个细节,但也很没道理。这两者间有什么关系呢?但杨先生说那个时候她就有一种安全感。这个细节之前对谁都没有提过,但我们可以推想,在他们漫长的夫妻生活中没有这一面吗?是有的。但这也是我的看法。杨先生的偏见太深,她自己也会忽略掉,我觉得这是她自己没有意识到的地方。
我可以这么说我的理解,但杨先生的口述传记,她是怎么叙述的,我只好怎么说。我可以打折扣,但不能编造“你们应该也有温情的时候吧”这样的事情。这部分是读者可以脑补的,不过好像都没有这方面的脑补。如果有一些阅历,或者说想象力,你就应该知道很多夫妻之间就是这样的真实状态。

西南联大高原社社员游海源寺合影。

杨苡离开以前,在孙以藻家的花园。
杨先生有很天真的一面,她会将一切都和盘托出,可以将自己身上的东西都自然地释放出来,这是我们常常所不能的,我们脑子里会有一个清晰的判断,应该如何,不应该如何。但杨先生有时候知道自己不应该这样,还是会说出来。比如说赵四,那个时候大家对赵四印象都很不好,对张学良恨得不得了,但她也很诚实地说看到她真漂亮。老太太真的是颜控没错,她老是在讲看到的人真好看真好看,像演员。
杨先生整个人很一以贯之,她的认知框架很早就定了,基本没有什么变化,稳定并且不复杂。比如最明显的,我的怀疑色彩很重,但杨先生相信的东西她就会非常坚定,也正是因为坚定,她的世界比较单纯,甚至因此给到她一层保护,也让她在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采取的立场比较容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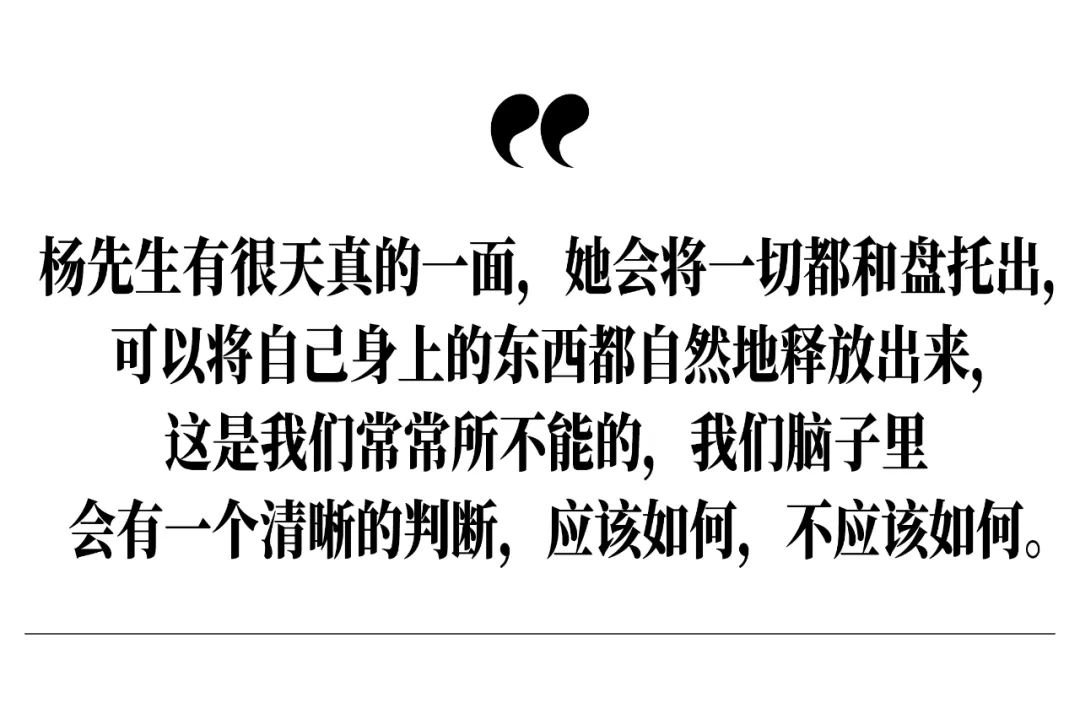
杨先生曾经有一个计划要专门写中西女校这一段的回忆,名字都想好了,就叫“翡翠年华”、这段是她最想写也最愿意写的,也觉得什么都可以说。可以说她的认知框架就是那个时候的底子加上巴金。当然我们讲的认知框架,是“应当如此”,现实生活中的为人处世,未必能够做到。比如杨先生明显受到《家》的影响,但是觉慧的举动不会发生在她的身上。在认知层面无数次发生了的事,在现实层面并没有发生。

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 是杨先生爱听的曲子,如这张照片中定格的 18 岁。中西女校的姑娘们穿着“绿色带有极密的本色小方格薄纱”做的旗袍,配白色皮鞋,象征春天的气息。杨苡接过毕业证书,“兴奋又激动”。她自此离开家,到广大的世界去,到广阔的人生去,遇见许多人,许多事。
杨先生其实是有自卑的一面的,包括她和大李先生的那一段,我的理解就有自卑的成分。她到最后都在猜测大李先生有没有爱她,一直到老都在自证自疑,一会这样想,一会那样想,我帮她分析呢她还很当真,绝对是个心结。
这就要说到她另外一方面的影响,就是她的母亲。她的为人处世、待人接物方面,很多都来自于母亲。到老了以后她自己都讲,说我越来越像我母亲了,包括对子女的严厉态度。还有怕姐姐。其实她和姐姐的关系很近,从那个时候她们相处的关系模式就已经定了,所以做口述的时候她会想姐姐看到了会怎么反应,她就缩回去了。比如小时候吃不饱饭,在仆人的桌子那里转来转去,人家喂她一口吃,这种事是她的创伤性记忆,她讲过很多次,她姐姐会觉得很掉价,但她没这个感觉。挺可惜的,杨敏如没有一部口述留下来,我在一些地方看到她的片段,也是记忆力极好,而且比杨苡先生更快人快语。

为杨先生做口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觉得很多东西值得记下。杨先生自己是作家,写了很多散文,而且都是回忆性的,和口述中讲的高度重合。但我觉得我要把口述做好,一方面是因为杨先生年纪大了,写起来更费力,另一方面是杨先生写文章的时候不像讲述的时候那么生动,在文章里口述时的很多东西流失了,太可惜了。
有读者说到看书的时候常常会有看到纪录片《九零后》里杨先生讲话时的那种感觉,这就是我想要的效果,一种双重的现场感。
一重是讲过去的事情,这种现场感不是任何口述对象都能带给你的,但杨先生的记忆有她的特点,高度场景化,会把你带到现场里去。第二重现场就是讲述的现场,我希望有这种感觉,有意保留现场说话的那种感觉、那种口气。在这方面我花的时间很多,比如说,在照片下面我加了大段的文字,是想要有杨先生就在那儿指着照片跟我讲的效果。

西南联大,大学一年级,杨苡和同学们在昆明翠湖公园入口处的合影。
书里我刻意地隐掉自己的存在,如果是我介入进来的那种访谈录的形式,会带出很多别的东西,比如我的视角。不过有意思的点恰在这里。我和杨先生的很多判断不一样,就拿文学作品的好坏来说,比如杨先生很崇拜巴金,我对巴金在一些方面很崇拜,但我不太喜欢他的文学路数,在我看来,还不够艺术家。比如说杨先生对现代主义的东西不大能接受,还有杨先生自己写文章和欣赏的东西,也是新文化里比较抒情化的倾向,我是不喜欢的。所以我把我这些看法过滤掉,只是在后记里比较委婉地写到,口述要呈现的只是杨先生的样子。
这本口述不可复制的地方,不在于我的能力,而是杨先生能全都跟我说出来。而且她讲是一回事,在生命的哪一个阶段讲是另一回事。比如 80 岁的时候不讲,90 岁可能就跟你讲了。杨先生活到那么大的年纪,可以说是比较极致了,什么都可以讲也什么都愿意讲。好多人活到这个年纪已经没有杨先生这样的记忆力和表述能力了,这些都是不可复制的。当然我也不会抹杀自己的功劳(笑),可能别人觉得很细微的东西,我都在放大,因为我觉得这些才是最有意思的地方。

杨苡家中的娃娃、摆件们。
和杨先生的对话很大程度是聊天,不是采访。就像我们平常聊天,什么大的历史背景什么的一般不会讲很多。另外,杨先生就是比较个人化,或者说她的重心就在这里。杨先生对于大时代的认知框架,和大多数人一样,同主流的描述基本吻合,但这不是她的兴奋点。至于她所认识的那些后来被认为有很大文学成就和地位的人,对于杨先生来说,重要的不是给比如沈从文以文学史的评价,而是我所接触过的那个人。对于我来说,最大的意义在于她是一个普通人,对于事情的反应方式、观感什么的,和大多数人是一样的。她不会不关心这个时代如何,但都是被动地被卷入漩涡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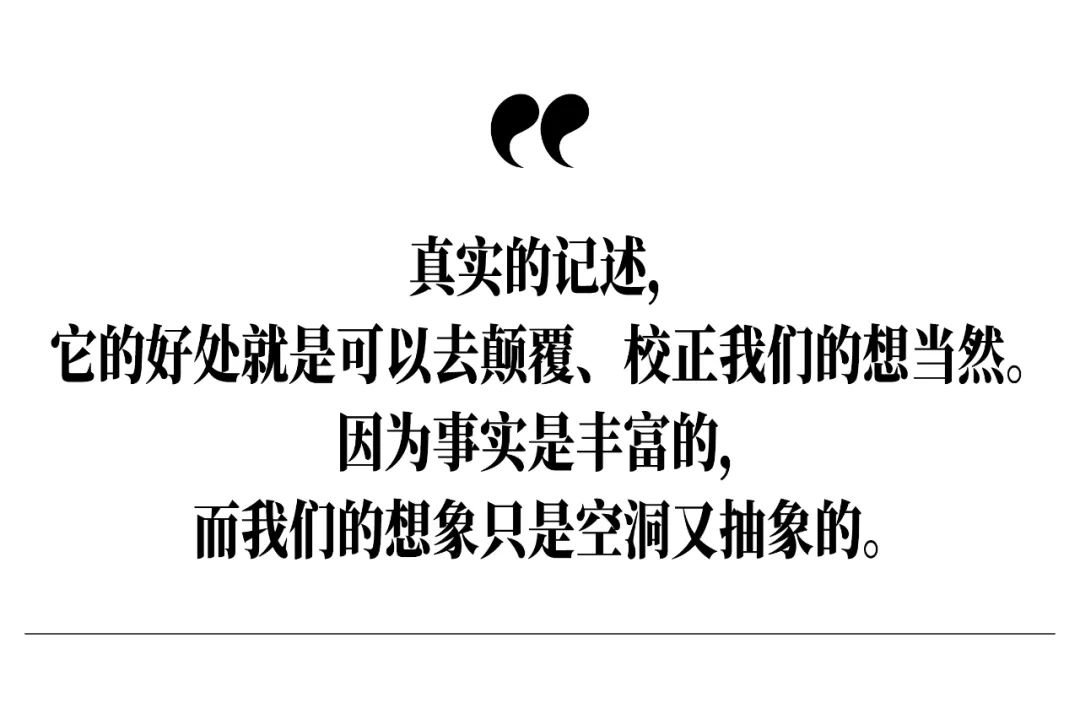
也许有一些读者觉得书里面没有历史的反思,因为这不是我需要的,我需要的是故事,而故事可以传递的信息比之反思要多得多。人们可以通过她的描述自己去想,而不是她直接给出一个结论。真实的记述,它的好处就是可以去颠覆、校正我们的想当然。因为事实是丰富的,而我们的想象只是空洞又抽象的。
讲到这段,我倒是想起来,就像很多人说羡慕杨先生经历的那种师友长谈的情景,或是我和她长期交往的这种经历,事实上这是时代的关系,也是我们对过去存有的滤镜。当时的人们没有现在的居住条件。像我读书的年代,要下乡学农,多少人都住在一起,加上 80 年代正值开放,大家相互之间想要交流谈论的愿望迫切。杨先生那个时代也是一样,不论是在中西,还是抗战时在西南联大,人们都有共同生活的氛围,这和现在很不一样。

杨苡上学时,西南联大的课堂。
我希望很多人读了这本书以后,能够对历史祛魅。我们现在讲的反思,很多时候是在教科书层面上的同义反复,不断印证一些已经被接收为公理的东西,再拿例子去印证。但 事实上应该要洗的就是教科书式的思维,破的就是标准答案。而故事是破掉标准答案、取消标准答案的最有力量的东西,这也可以是反思。
在这个意义层面上,我觉得叙述本身就是力量。还有一个超出书以外的希望,就是要是有人觉得我家里面的人事也可以记一记,那就太好了。你说这地球上曾经活过多少人,活着的人比死去的人少得多,那么多人来过,却好像一点存在过的痕迹都没有。如果都来记述,很多东西都很有意思。
杨先生后来老跟我讲:“你花这么多时间做这个东西,听我说来说去的,都没什么大事情,是不是耽误了你的时间?你自己的事情都没有空做了。”因为她的医生还跟她说,经常讲这些事情对你有好处(记忆力训练),她总觉得自己是得到了,“你不是亏了吗?”我开玩笑说:“杨先生,我们是双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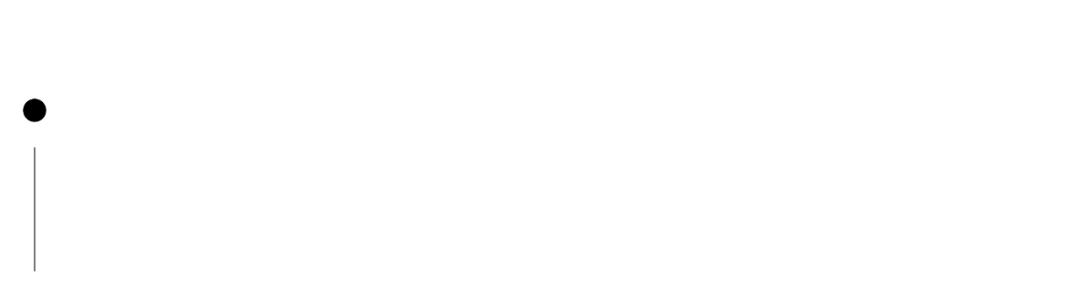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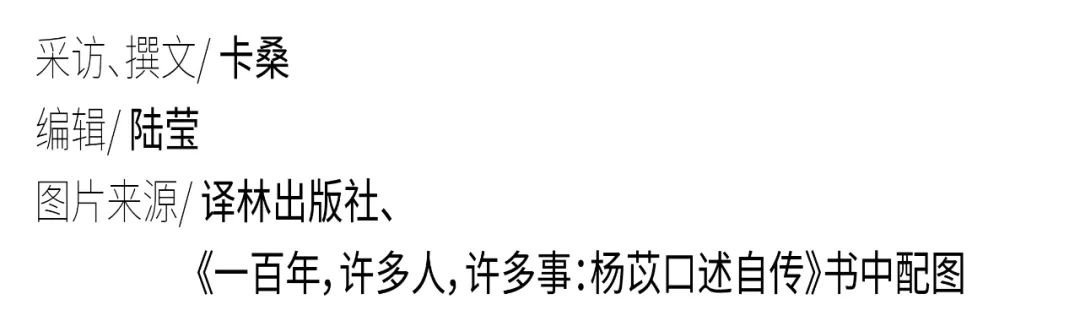
相关:
孙立平:中国真的存在内需不足吗?内需不足,好像现在已经成了一种定论。虽然在内需不足形成的原因上,人们有种种不同的看法,但对内需不足这种现象的存在,似乎没有人进行怀疑。包括我自己,原来也是人云亦云。但事情难道真的是这样吗?首先我们得..
突发绝症!46岁“天才学者”:我即将告别这个世界了3月15日下午,青年历史学者李硕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了一则自己突发绝症、即将离世的消息,“目前有大学旧友们帮我料理生前身后事,一切完满具足,无劳挂念。”李硕希望朋友们别发信息、打电话给他,他已无力回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