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某种意义上而言,我们必须承认人类的一种“不幸”,那就是生命是有限的,我们只能活在自己的时代里。
但可幸的是,我们可以借由历史去回顾、去检测人类经验的广度,去寻找生命的诸多可能性。
可惜的是,往常我们对于历史的理解总是倾向去寻找标准答案,寻求某种盖棺定论的确定性,甚至会因为找不到确切答案而焦虑。
然而,我们不曾留意的是,就算能够获得所谓的“确定”,或许也会因过度设限,反而失去了探知生命多样的可能。
在看理想电台的一期节目中,主讲人杨照说,他会经常问自己“你怎么可能甘心,就这样过一辈子?”他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和感受,不过只是这个真实世界里非常微小的一块。他从未停止对世界的“饥渴”,就像他后来常说的,“年轻人最重要是知道世界有多大”。对世界变幻莫测的瑰丽见识愈多,对自己便愈加忠实。
这或许也是促使他对治学中遇到的“标准答案”不断质疑发问的原因。
所以,当人们更倾向于将唾手可得的“标准答案”照单全收的当下,杨照呼唤大家重新思考:答案从哪儿来?跳出自己所处的时代,去感受不同时代人们的多样生活。
这或许能让我们活得更幸福,毕竟,我们不再会因找不到“标准答案”而困惑焦虑,也不会因达不到所谓的“标准”而自卑气馁。
这么说来,真正能让人心安的,并不是一个机械植入的“标准答案”,而是建立在独立思考之上的清晰的求知过程。

讲述 | 杨照
来源 | 《重述中国通史》
(文字经删减编辑)
01.
坦诚面对历史的局限,你或许会更自由
我曾经写过一本比较少人知道、更少人读过的书,叫《推理之门由此进》。
虽然这本书很多人都不知道,可是我自己写得非常过瘾。它是在解读4本我自己选出来的推理名著。年轻时候的我,唯独对推理侦探小说非常着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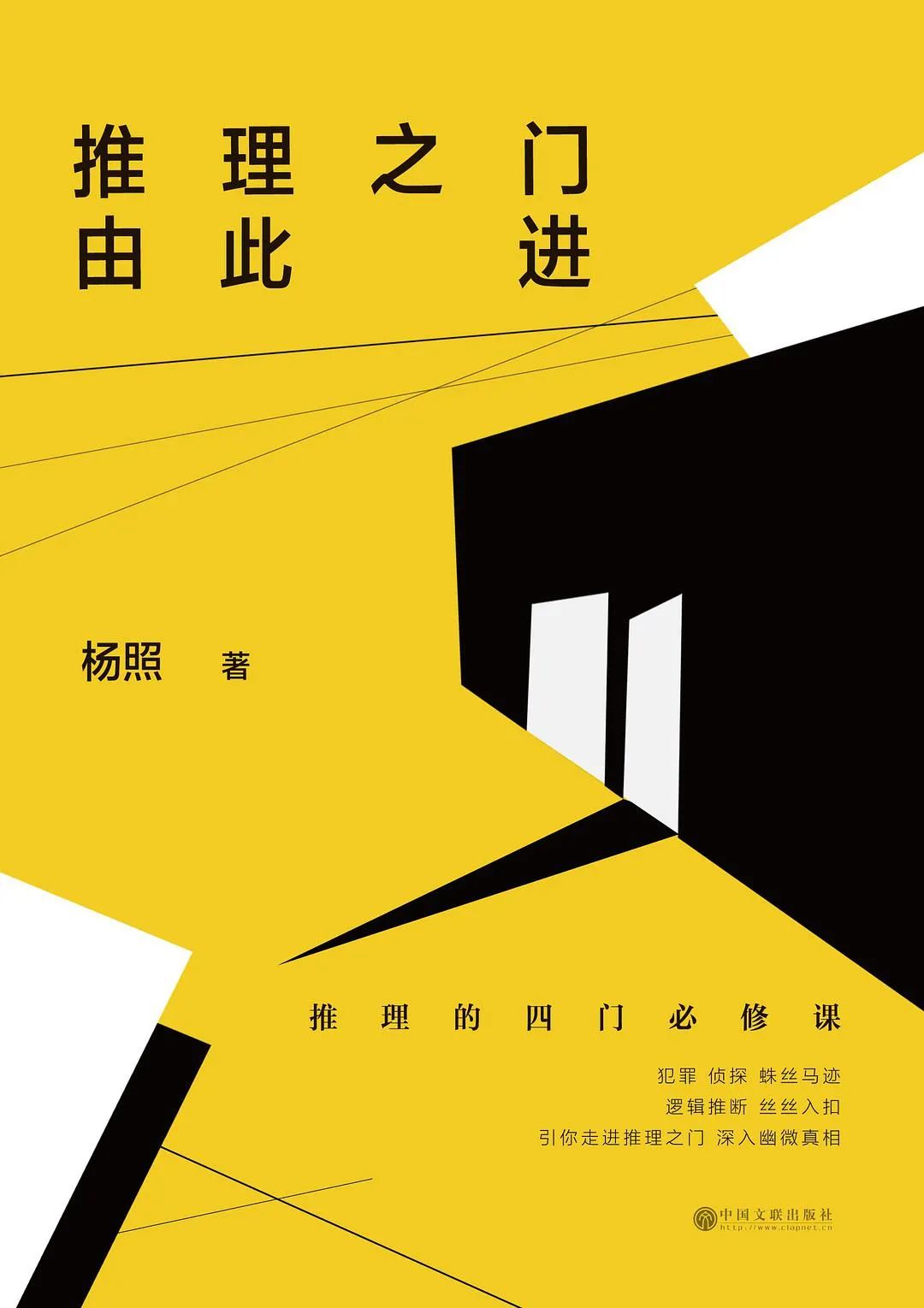
《推理之门由此进》,中国文联出版社
推理尤其是探案背后需要的是什么?那就是严密的逻辑训练。这是独立思考最重要的基础。你要懂得如何收集资料,分析资料,如何有逻辑性地去思考,并且找到可信的结论。
在台大历史系,我们有一门必修课,叫“史学方法论”,是历史系学生要学的研究方法和方法论。那个时候我们的老师杜维运、黄俊杰,再三地提醒我们,这门课是台大的骄傲,与别的学校就是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呢?除了台大以外,在其它学校的历史系,这门课都叫史学方法,但在台大,我们跟别人不一样,坚持叫“史学方法论”。
“史学方法”跟“史学方法论”只有一字之差,但意义大不相同。
“史学方法”表示这是一门技术,所以这门课在教你什么是史学,什么是史学研究,还有教你一套方法,让你自己去进行史学研究,这叫做史学方法。
而史学方法论,是一门原则,甚至是哲学领域的探索,而非单纯的技术。
史学方法论要问的是:历史知识是怎么形成的?如何检验?历史如何成为可能?
后来,我发现历史其实是一套“大推理”,意思是说你要去面对过去所留下来的众多可信或者是不可信的各种资料、各种不同的线索。而这些资料和这些线索,甚至就像是推理小说中会遇到的线索,很可能是犯案的人刻意误导的,或者有的时候是目击者不小心误导的。
一个史学研究者的任务,当然不只是接收和传达既有的答案,而是必须小心翼翼地面对所有的资料,了解不同资料的各种不同的来源、不同的说法。最后,在这重重荆棘般的环境中努力做出至少可以说服自己的判断来。

我最初开始读历史的时候,发现自己有一段时间其实学不下去,为什么?因为我会一直不断地怀疑,我应该相信这段话吗?我应该接受这样的说法,并把这当作是历史的事实吗?我还是会想去找其他的资料来印证,并思考到底应该用什么方式才能消除自己的怀疑。
所以,对于史学,虽然我当时还很年轻,却渐渐地抱有了一种无奈的态度——如果要真诚地面对历史,诚实地面对史学,就要像侦探一样承认,有些案子就是破不了,因为没有足够多的线索,没有足够多的证据。或许我们心里会很不舒服,很想要探究出真相,但我们永远都无法知道。
所以,我们只能够依照既有的线索、证据尽可能地去找出最好的答案。所谓最好的答案,也就是最合理的可能性。不要再认为,历史应该告诉你确切的真相。
当然,这样也就使得史学的探究必然存在很多的缺漏,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存疑。因为存疑,所以就不能说太多,更重要的是不能说得太明确。
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虽然有这么多的存疑,但对于基本上所有的历史事件,我们都在持续地累积、选择和分析资料,从资料中寻找最合理的推论。
长期以来我抱持着这样的态度,面对历史,面对史学。我很想用我自己所认为的这种对的推理,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讲中国的历史——
不是传递答案,而是呈现如何追求答案的过程,同时也将追求出来的答案放回到追求答案的过程当中,将答案和过程一并呈现在大家的眼前。
02.
面对诸多的不确定性,
可以试着从过去找答案
一般的教育体系里对历史的讲授方法,往往把历史视为固定的人名、地名、时间和事件的堆砌,试图用一套标准答案告诉你“什么时候、什么人、发生了什么事”。这种枯燥的形式,无疑让很多人对历史越发无感,甚至非常地疏离。
如果历史就是这样的话,老实说,的的确确非常无聊。一个糟糕的学习方式就是让它充满固定答案,每一个固定答案就必然排除了许多相关的错杂现象,还有更丰富多元的可能性。
但如果说历史的学习不应该是有标准答案的单纯记诵,那么我们应该学什么呢?或者说,回顾历史能让我们收获什么呢?
这就牵涉到更根本的学习历史的目的,在我看来,有两种:
其中一个目的,是通过历史,来了解、掌握人类的集体经验,让我们今天在生活中有所参考。
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只知道某个朝代在哪一年、经由谁推翻哪个朝代而建立,这样的知识对于我们如何看待生活、看待政治、看待社会,恐怕很难有什么实质的帮助或影响。
如果要让历史对于现实产生提醒借鉴的作用,需要的不是这些固定的死知识,而是要从历史当中整理出变化的现象和规则——看清楚人类在过去遇到过什么样的事情,做出了怎样的反应;因何种动机产生了哪些行为,这些行为又造成了何种后果。
只有努力整理出规则,我们才能对比发现今天出现了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可以如何反应;或者如何去评估理解别人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反应。
真正有用的是归纳之后的原理和原则,而不是单纯去陈述个案的资讯。
不过如果学历史,只是为了要对现实生活有所帮助,其实我们也不需要学习那么长、那么复杂的历史内容,我们需要的只是从历史里简化、归纳变化的规则。
所以,有种可以跟现实发生关系的历史学习,是用言简意赅的方式去萃取历史,只留下历史哲学,比如西方18、19世纪的历史哲学。
然而,那些风行一时的历史哲学,后来几乎都被扬弃了。
因为历史哲学整理的是普遍规律,既然是普遍的,就应该是既适用于过去,也适用于现在,同时会适用于未来的。
但是这么久以来,所有这些历史哲学的常识却不断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一套历史哲学能够借由整理出来的规律,准确地预测未来。
毫无例外地,每一条从历史里归纳出来的定律,都在时间中被证明是不准确的,或者说都是经不起考验,被推翻了的。历史哲学纷纷被它们无法预见的人类行为的多样性给打败了。
03.
我们的一种“不幸”,
在于只能活在自己的时代里
所以,学习历史的目的,比较能说服我的是第二种——借由历史去检测人类经验的广度,去感知人类经验的多元和多样性。
于我们而言,很“不幸”的是,人的寿命是有限的,你只能活在自己的时代里。
但我们不是第一代活着的人类,也不会是最后一代,历史的其中的一项作用,是向我们完整地全幅地显现人是多么奇特,而且独一无二。
我们建立了文明,摆脱了本能的约束,继而创造了其他动物绝对没有办法比拟的复杂性。虽然人类自然本能的同质性很高,文明却可以天差地别。
一棵树所需要的水分、阳光以及从土壤当中得到的几种化学成分通常是固定的。同样品种的树会长出相似的树皮,同样分枝生长的树枝,还有形状相同的树叶。
自然界当中同种的动物基本上用相同的方式觅食,吃着相同的食物,而且吃东西的方式也大致相同。
但人不是这样的,人给自己披上了各式各样的衣服,可以吃成千上百种食材,并把这些食材用数不清的程序和手法来制作,也用数不清的方式来进食。
透过历史,我们看到了真实的、活生生的人类累积,并且产生了丰富多样的经验,这才是人的完整面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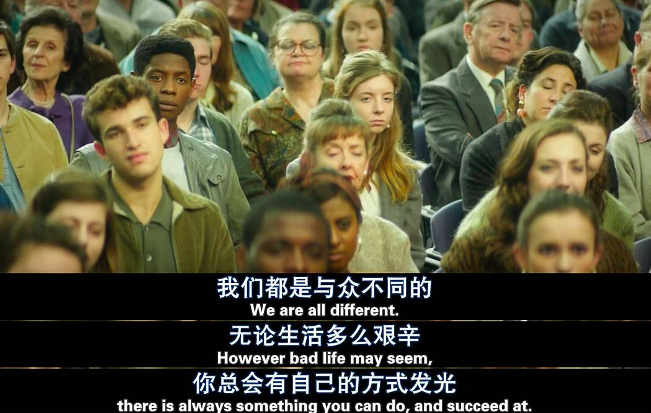
抱持着这样的目的来学历史,相较于前一种目的,就会得到很不一样的历史。
前一种是简化的,强调且凸显“同”,专注地去找出相同的现象,以便归纳为人类行为的律则。
后一种刚好相反,要尽量保留复杂性,强调且凸显“异”,也就是“不同”,找到不同的现象,并收入到历史多样性的宝盒里。越是不一样的,就越应该被写进历史里。
从认识人类多元性的角度出发,就比较容易明白,为什么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历史,因为不同的时代会用不同的方式来整理人的经验,凸显出不同的面相、不同的重点。
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简单地认定前人所写的历史就是唯一的答案,而没有注意到他们会有自己的动机或理由来这样看待历史、书写历史。
尾声.
时间不断对我们提出命题,
历史则是命题的答案
历史不会直接作用于现实,但刻意去否定历史的社会,常常会得到危险破坏性的结果。比如秦始皇统治时期用焚书去毁灭历史,又比如希特勒主政时期用屠杀去取消部分历史、操纵历史,这些都成为了历史上的阴影。
所以,比起关不关心历史,更重要也更关键的,是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关注历史。
一种态度是,为了在历史里寻找、修订标准答案,要把历史写“死”了,不准人质疑,也不准人改变,这是一种态度。
另一种态度是,我们想在历史里挖掘出许许多多可能的答案。
正如诗人杨牧在《时光命题》里写的,时间对个人、对社会一直在不断地出考题。而历史是什么?历史就是过去的人针对这种时光命题所提出的各种不同的解答,各种不同的答案。我们进到历史里去,是为了去探索、整理这些不一样的答案。
前者的态度,必然制造出凝固的越来越死气沉沉的社会;而后者,则是让每一个人经由对历史的好奇与探索,放大视野,刺激多元的创造力——这当然会是一个比较好、让人活得比较幸福的社会。
相关:
《红楼梦》中只出场一次的元春,为什么如此重要?元春是《红楼梦》中唯一一位被正面塑造的宫中女性,对她的直接描写,小说中只出现两回。这位宫闱深处的女子与读者仅有“一面之缘”,却在千万人心中留下了难以忘怀的悲叹。元春。来源/87版《红楼梦》剧照高贵荣耀..
三十岁那年,我出家了野村馨是一个三十岁的小伙子,在设计公司上班,每天觉得身心倦怠、前途渺茫。突然他决定到以严厉著称的永平寺修行,在一日日的苦修之中,荡涤内心的欲望。一年后他重返职场,在通勤的电车上完成了这本回忆录《云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