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时候,读书君总想离开老家,主要是为了离开那种看上去很没意思的生活——隔壁的大爷遛弯儿多年,每次都走相同的路线;保安大哥坐在保安亭里看着外面,从黑发看成了花白头发。世界那么大,生活那么丰富,这么度日可太没意思了。
当然,那是一种孩童时的天真幻想,等尝过点酸甜苦辣,见识过成年人的生活后,才发现那些中老年人,真懂得生活之道。
生活之道是什么?作家高军的新书《咕噜咕噜下春山》中,有一个答案:哪怕处在下坡路,也要带着玩乐之心。
他写秃顶的美学意义,写在保安亭门口种葵花的保安,写泰然自若与儿子谈论死亡的父亲。瞧,这种发现生活乐趣的能力,可把年轻人们给羡慕坏了。
下文摘选自《咕噜咕噜下春山》,经出版社授权推送。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
01
谢顶是一个男人成熟的标志,啊!
老实地说,我很羡慕中年谢顶的朋友,甚至在羡慕之余还有点嫉妒和恨。一个中年的男人,谢顶不是一下子开始的,它简直可以说是一场盛大的季节转换。这种转换可能起源于某一天早晨起床,发现枕头上几茎头发,或者是梳头时发现梳子上缠了头发,甚至是清理下水管出水口时,发现水下不去,原来是被落下的头发堵住了。你拈起一撮头发若有所思。
这一切都进行得静悄悄的,像初春时枝头第一茎暴出的新芽,像冰层下涌出的第一道清泉。你能感觉到风真切地抚摸到你的头皮,感觉到雨水滴在头皮上的清新。头发由青春阶段的旺盛渐渐变成稀疏,然后在发际线前面出现一只美丽的猫头。
每当我看到一个朋友头部出现这样的猫头时,我都忍不住想在他前额亲上一口——如果把一个人的头部比作一座山,那么这时一个男人的头发正在进入最美丽的季节。恽南田在他的《南田画跋》中说:“春山如笑,夏山如怒,秋山如妆,冬山如睡。”谢顶是一个男人成熟的标志,啊!人生的秋天开始了。
这种转变往往需要好几年才能完成。最近一次和朋友聚会时,我发现许多人的发际线都出现一只美丽的小猫。当我对他们头部的美表示出惊叹时,收获的却是他们的怒目而视。这种事情让我很郁闷。谢顶的朋友似乎对这种事情很介意,甚至是有点痛不欲生的感觉。他们谈到了自己采取的措施,尝试各种民间验方(白兰地、鸟屎、辣椒、生姜、陈醋,勤梳头,戒烟戒酒,早睡早起,章光101,各种中西生发剂……),将这一系列试验都在头上做完之后,头皮仍然不可遏制地显露出来,像突出海平面的孤岛,又像覆雪的富士山。

《隐秘的角落》
这时他们才如梦初醒,于是想出各种办法来补救。奇怪的是谢顶它往往是谢在中间,很少有人谢在后脑勺或左右两边。谢在左右两边那是斑秃,得上医院治了。于是谢顶人主要是针对发型中间这片空白区域做挽救。最流行的是“地方支援中央型”,这种发型还有一种叫法是“谢广坤式”,就是把周围的头发留很长,然后尽可能往中间拢,再用发胶把它胶住。日常活动时没有什么闪失,但一旦剧烈活动,周围头发散落下来,就造成了不可收拾的局面。最常见的一种是和老婆打架,被她一把薅住那可不是玩的。
有一次我到上海去见一个很多年没聚的朋友,晚上一起在饭店喝酒。那时他刚送完女儿到美国去读书,谈到他这么多年在上海的打拼,谈到他生活的压力,谈到年迈的父母,谈着谈着头慢慢低下来,原来围在中间的头发不可遏制地崩溃下来,微黄的头皮露出来,然后慢慢地开始打起盹来,给人的感觉特别颓唐。我推了推他说:“哎!不早了,你还要坐地铁呢!”他忽然惊醒后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把头发往中间拨。他问我:“你认识回宾馆的路吗?”我说:“认识!”出来后,我们在外面握了一下手,各自走散。走了几步,我转过身看他一边走一边在整理头发。
另一种谢顶朋友发型是这样的,大部分出现在搞艺术或者被艺术搞的朋友中间,那就是放弃对中部头发的挽救,极力延长脑袋后部头发的长度。平常披散着,像一个河童,又像带发修行的武松。参加激烈的活动时,可以将后部扎成一个小辫,一直拖下来,也是怪标致的。
许多中年男人对谢顶有一种恐慌。我有一个朋友,他从年轻时就对谢顶非常恐惧,因为他听人说谢顶是遗传的,他的爷爷一直到他爸爸都谢顶,他弟弟在二十来岁就开始谢顶了,所以他经常做梦会梦到头顶头发掉得一根不剩。半夜里他会跑到卫生间里对着镜子左照右照,然后用手指摸着头发十分珍爱地梳下来。尽管他那样爱惜,可一过三十五岁,就开始谢顶了。他呼天抢地,到处寻医问药。有一段时间沮丧到不想出门,就是出门也是无论春夏秋冬都戴着帽子。家里的玄关有个柜子,柜子里放了几十顶各种各样的帽子。每次出门前他会站在玄关镜子前面试戴帽子,这种试戴行为要进行好几十分钟。
因为我是朋友圈中特别擅长给人进行心理治疗的人,大家伙儿就公推我给他做一次心理治疗。起初我很抗拒,我说应该由一个谢顶的朋友去解劝他,这样效果可能会好一点。我的理由是患者和患者之间更好沟通。他们说你可以从美学角度给他做一次心理治疗,再者说了你是一个画家,无论是从美学还是美术角度,你都是最有发言权的。于是我就在家里做了点功课。我把平常收集的中国画中关于谢顶题材的绘画整理了一下,主要来源于《晚笑堂画传》和《李可染画集》,还有我自己画的一些对照草稿,做了个集子,就上这个朋友家里去了。

李可染《松下纳凉图》
这位朋友在我进门后已经将帽子戴上了,所以我没办法看到他究竟梳了什么样的发型。我以前认识一个人一直戴帽子,他在我的印象中除了戴帽子没有其他的形象。后来他去世了,我去参加他的追悼会,真是悲喜交集。悲的是失去了一个朋友,喜的是终于有机会看看他的头发。结果他躺在一具水晶棺材里,头上仍然戴着他经常戴的帽子。
那天我问这个谢顶朋友的第一个问题是:“谢顶美不美?”他果断地回答:“不美。”我接着问他:“你为什么觉得不美?”“那你为什么不秃一个?”他反问。我说:“不是我不想秃,我不可能到理发店让人在中间剃掉一块对不对?所有不自然的东西都不美!我不想要不自然的东西。”
我摊开收集的画册,然后一张一张翻给他看:“这个都是我们中国画大师的作品,你看看里面的人物有哪一个不谢顶?我们的画家为什么去画这些东西?”他摇摇头。我说:“那是因为这样画才美!你看看刘松年的《罗汉图》,那里面的罗汉是不是比你秃得还要厉害?

刘松年《罗汉图》
”他凑近看了一眼说:“那又怎么样,罗汉都是从印度过来的。那边人年纪轻轻就秃了。这个没有代表性。”“好好,我们放下罗汉不说。那我问你老子是不是中国的?”他说:“中国的呀!”“好,下面我们看老子。”我翻开《老子骑牛图》,我指给他看说:“秃不秃?”他说:“秃。”
说完他跟我商量说:“风哥,能不能不要用‘秃’这个词,我听了扎心。”我答应他说:“好,不用!换个名词,叫‘谢不谢’行吗?”他说:“行!”我接着说:“老子谢不谢?”他转过脸看我说:“谢得蛮厉害的!”我说:“你对于美的认识是有偏差的,你的美感认识是建立在世俗和西方不成熟的美学经验上的。你看过《阴翳礼赞》这本书吗?”他摇摇头。
我说:“谷崎润一郎就说了,我们东方审美跟西方审美是不一样的,就拿牙齿来说,过去日本美女的牙都要涂得黑漆漆的。一口长得七扭八歪的牙齿才是标准美人。西方那样整齐的白牙在日本反而是残忍刻薄的象征。谷先生说了,西方人的白牙丑得像厕所的地砖似的,无任何美感可言。所以你看到现代日本女孩子牙齿都不太好,人家也没有忙得全民去整牙对不对?”
他听了点点头。为了更有说服力,我把《李可染画集》中的图片拿给他看,说:“你看看这里面的高士,不管是纳凉还是观画、赏莲,有一个是不谢的吗?”他俯身研究了半天说:“好像是这么一回事。”我说:“主要是观念,观念一转变,你对美与丑就有深入的认识了。”
我指着他家里博古架上的灵璧石说:“就拿这个石头来说,你告诉我它美不美?”他说:“不美我弄它在家里干吗?”我说:“这石头有‘石有几德’的说法,其中一德就是要丑。不丑它就不奇,不奇就没办法高古。所以人谢了顶,这个人自然就高古起来。我这里有两张图,我画的。这第一张中的高士都是谢了顶的,第二张我把头发都添上了。你觉得哪张好看一点?”他指了指第一张说:“还是谢了顶的好看。”

喝了一口茶我接着说:“这几张图看过了,我再给你看看《晚笑堂画传》。你看看,从前到后的人物,有几个不谢顶的?这个仰观的老者,多么明显的地中海秃呀!哦,地中海谢顶呀。”他已经没有在意了,很认真地往下看。“你看看寒山、拾得,我们中国的吧。两人都谢顶。”他沉吟了一会儿说:“听你这么一说,我的信心好像又回来了。如果我发型弄成画上这样,你看看我穿什么比较搭呀?”

我说:“就棉麻制品,中式的。手串、佛珠什么你有吗?”他说:“有有,要不你等会儿帮我挑一串。你今天这么一说,我心里的包袱就放下来了。”我说:“这个人啊,少要轻狂老要稳。你这个发型再加上衣服这么一搭,出去谁敢说你没修行?多大岁数的人了还为这点事情犯愁,不值当的。”“那我这今后真不要戴帽子出门了?”“天实在太冷还是可以戴的。”
02
不让我回老家种地,我死给你们看!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最艰难的工作莫过于两种:一是当值班室的保安,二是开电梯。现在电梯大多数没有专人开了,只有医院里还有。 电梯落下来,里面有个胖大婶坐在一个方凳上面无表情问你: “几楼? ”然后开上去,这么狭小的空间,视线看到的只有笔直的不锈钢四壁。 这种工作让我想想都觉得害怕,我觉得我只要开上三天肯定会疯掉。
另一个最让我感到害怕的就是当值班室的保安,也是在一个同样狭小的空间里,像长在里面一样,车来了把杆升起来,车进去放下; 有人来就喊他登记,问他找谁,哪个单位的,留下他的电话号码。 一年三百六十来天,周而复始。
以前看到一个人写值班室的保安,说他无聊到猜汽车的号牌尾号是单还是双,猜对了就高兴半天,猜不对就沮丧很久。坐久了起来活动活动,可不敢走远,万一来人或者来车怎么办?拿把扫帚把值班室周围一两百米的地方扫一扫。没车没人的时候,掏出指甲刀修指甲,但指甲已经修得很完美了,于是只好悻悻地收起来。
看见一个熟人带小孩过来,拦住他让孩子叫爷爷,不叫不许走。孩子躲到大人的后面,大人就把他从后面拽出来,罚他叫一声。偏这个孩子犟,死活不叫。保安也只好让他们过去了。
看书、听收音机都不行,对着值班的位置有个监控。我叔叔原先在南方打工干的就是门卫这个活儿,他说最受不了头顶上有这个东西。他跟我堂弟说:“如果不让我回老家种地,我就索性喝瓶农药死给你们看。”
于是就回来了。回到家里老房子屋顶已经漏了,树根都长到堂屋里来了。花了几万块钱把房子修好,修房子的钱正好是他那两年上班的积蓄,但就是这样他也很满意。他跟我说:“真的,再让我干下去,我真会疯掉的!我喜欢在地里,虽然说又累又挣不到钱,可是我抬腿就能走啊!”
前天早晨,我走到家附近建行那里,忽然发现香樟树下面长了一棵半人高的向日葵,在晨风中晃晃悠悠的。我驻足观看,这时建行角门值班室里走出一个保安,站在我旁边说:“我种的,许看不许动哦!”我说:“这花挺好看的,怎么想起来种在这个地方?”我指指香樟树。他说:“这四周都是水泥地,没地方种。而且种在这个地方,我一抬眼就能看到。”我问他:“那晚上你不值班的时候让人采了怎么办?”他说:“我关照晚上值班的人帮我看着。你看看葵花盘子都长出来了。”
我说:“这一天到晚坐在这里面是受罪哦!”他说:“那没办法,没本事嘛!到我这个岁数还能干什么,要吃饭啊!”接着他说:“这个活累倒不累,就是熬人。一天到晚离不掉人,从我值班室那边看过来,只能看到这个树根。我在这里都干三年了,天天看这个树根,今年想给它变变样子,就撒了一粒种子,谁知道它还长起来了。才开始我以为它长不大,谁知道后来越长越好。没事的时候我给它上肥,你看长得跟地里一样好。这几天开了花,我要不是盯着早让人摘走了。一般男的都不喜欢花,女的嫌麻烦。所以我一看到人看花,我就出来说两句。”
我笑笑说:“我就是奇怪,这个树根底下怎么长出花来了。”他说:“哎!你别看,种上这个向日葵,从我坐的那个角度看过来就不一样了。原先我以为城市里没有露水,可我每天早晨接班的时候,一看叶子是耷拉着的,跟我老家地里一样,上面露水滚来滚去,太阳一照都刺眼。老话怎么说?‘一棵草顶一颗露水珠子’,你说有这个话吗?”
我点点头。他接着说:“天好的时候还有蜜蜂来采蜜,叮在上面。我数过最多的时候来七八只,小屁股上面有黑道道,一拱一拱的。马上盘子里面有籽了,我得当心麻雀来啄它。我也不是小气,就一个盘子,就说收籽能收多少?好玩呗!上次有只蝴蝶来了,漂亮极了。翅膀上有蓝道道,都闪光,宝石似的。我趴那里动都不敢动,它围着花绕来绕去地飞。后来有辆车要出去,它吓跑了!”我说你是个诗人,他挠挠头说:“哎呀!让你给说得不好意思,我就是无聊找人聊聊天。好,回见!”

保安栽种的葵花
昨天晚上下了一场雨,早晨我从建行角门那里经过,发现花让人给撅走了。我停下来看,那个保安出来说:“花昨晚让人给偷走了,早知道我给它撒点儿农药就好了,吃死这个王八蛋!”我说:“以后种点别的花,矮牵牛、波斯菊。”他说:“不赶趟了!我明年还种,结籽的时候就打药,看他还撅不撅了。”
03
人啊,真是不经活
过了冬至我爸的身体就不太好,头晕,夜里盗汗,不想吃东西。我劝他去医院看一看,他说休息一下可能就好了。我去社区医院找到过去给他看病的医生,开了点“玉屏风”,还有一些其他的药吃了也不见效。盗汗更严重了,夜里睡觉一身衣服都湿透了。我打电话给我姐,让她联系了一家医院立刻住了进去。住进去以后第一天是各种检查,首先是核酸检测,然后是核磁共振、CT、B超,等做完以后就快到下午了。病房的窗外,是一片冬青树林,看着日影在树林后面慢慢暗淡下来。冬青树林里的南天竹已经结了红果子,枝头上像着了火一样。
我问爸爸想吃什么,他摇摇头。我说你从早上就没吃东西,我去看看下面有什么吃的卖。我去食堂,给他买了一份青菜肉丝面,他看了看说不热。我拿到走廊的尽头一个微波炉上热了以后端进来,他吃了一点就睡了。我姐示意我出去一趟。她问我:“你看老爸这次能不能挺得过去?”我说:“这个不好说。”我姐说:“那有些准备工作要提前做,省得到时候抓瞎。”“做哪些准备工作呢?”“比如你可以问一下老爸百年以后想葬在哪里,有什么未了的心愿。”我说:“这个现在问不好吧?”“有意无意的。”“你怎么不问?”“我怕老爸骂我——我看有些人家的老人很达观,子女把寿材、寿衣做好还拿给他们看,他们也没什么意见的。”“好,我看看时机吧。”
到了晚饭时间,我问我爸:“面条不想吃,想不想吃其他的东西?不吃东西身体怎么扛得住?”我爸想了一会儿,说:“我想吃大白菜炖粉丝。”“那个没什么营养,晚上大姐炖了鸡汤来,你喝点鸡汤吧。”“我就是想吃一点大白菜炖粉丝。记得我在新兵连的时候,到厨房帮厨,我的一个老乡正在熬猪油。他让我拿个脸盆来,给盛了一盆猪油。我端回班里放在床下面,冬天猪油很快冻上了。每次去打菜的时候就来一勺,热菜打到盆里,猪油化开了,菜别提多香啦!我就想吃这东西。”
“那我让我大姐给你烧吧!”我说。晚上我姐送饭来,给带了一饭盒油渣烧大白菜,里面放上了粉丝。我爸尝了一筷子说:“不是那个味——里面没放猪油吗?”“放啦!放得不多。猪油吃多了不健康。”“这个菜烧得一点味道都没有,先放着吧。等晚上我想吃的时候再吃。”
晚上我给我爸打来洗脚水,他说:“我自己来吧!”还是觉得头晕,几次差一点把盆给踩翻了。我说:“你别逞强了,我来。”我帮他把脚擦干,他忽然感叹说:“人怎么忽然就老了?我觉得自己还年轻。我在新兵连当班长的时候,就是因为军事动作好,被挑到教导队去的。单双杠、队列、负重行军不在话下,那会儿真是浑身是劲。不管怎么累,睡一夜起来屁事没有。唉……这个人啊,真是不经活,眨巴眼工夫八十多了。”
“我还不一定能活到你这个岁数呢!”
“哎,也不要活太大,给子女添负担。吃又不能吃,也不能到处跑。有啥意思?跟我一个火车皮拉去的战友,现在只剩下我和你大头叔叔了。”
“大头叔叔现在怎么样了?”
“也不行啦!七十多岁的时候还骑着自行车到处跑,说不行就不行了。我老想着去看看他,可是我这腿脚也不听使唤。我耳朵不好,他耳朵更不好。你说城门楼子他说屁股头子,聊起来费劲!”
“等你好了,我陪你一起去看大头叔叔可好?”
“这一回能不能出得去还难说呢,前几天晚上我胸闷喘不过来气,浑身冷汗直冒。我想今晚差不多要交待在这儿了吧,不过转念一想,就这样走了也幸福!利利索索的——”
“你害怕吗?”
“不怕!没什么好怕的。其实我思想上觉得自己还不算老,应该能跑能跳的。但是这个身体不给力了,如果能甩掉这身臭皮囊也不错。人不可能违背自然规律的,如果人都活着,这个地球上怕是连站的地方也没有了。”
“想过将来百年之后在什么地方?”
“不要去公墓里,这一点你记好了。又贵,过了二十年还要续费。你想想看二十年以后你多大啦?每年清明、冬至你还得往那儿跑,多麻烦。你得看子女有没有时间开车送你去。了不起到了孙子这一代还去,再往下,去也是勉强去的。不如撒了,或者种一棵树当肥料也好。省得让他们赚钱。”
我爸说完想了一会儿,他看着我:“是不是医生跟你说什么了?”我说:“没有什么——你别多心。”他接着说:“如果你接受不了撒掉或者埋在树下,跟你奶奶放在一起也可以。我自从当兵出来,就没有在你奶奶身边服侍她老人家,都是你叔叔养老送终的。我呢,只不过平常寄点钱回去,没有尽到孝敬老人的责任。活着不能尽孝,死了以后就陪陪她老人家吧!我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能活到八九十岁。已经很够本了!”
我说:“话虽然这么说,佛教说‘成住坏空’,人有生老病死,诸苦合集这个是避免不了的。但是感情还是接受不了。”我爸看看我:“每个人到世上来,都要受这么一回,我受我的你受你的,谁也代替不了谁。我也知道你问我这个话是什么意思,百年之后的事情,你跟你姐商量着办,怎么简单怎么办。亲戚之间远的就不要通知了,都挺忙的。”


《咕噜咕噜下春山》
作者:高军
出版社: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年: 2023-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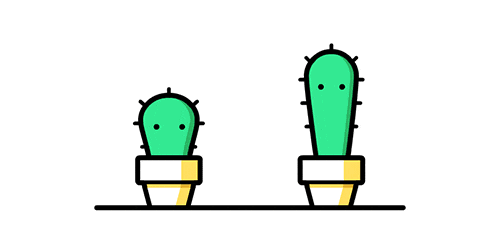
相关:
齐格蒙特·鲍曼:为什么我们正在失去爱的能力相信绝大部分人都对齐格蒙特·鲍曼并不陌生:无论是“怀旧的乌托邦”,还是“流动的现代性”,抑或“被围困的社会”等概念或书名,当然还有《现代性与大屠杀》这部名著。在他的最新访谈集《将熟悉变成陌生》中,最..
秋天来了,我想随风远去,可我哪儿都没去“城市的黎明降临了,在灰蒙蒙的天色中,一群人等着早班公交车的到来。这时候,整夜都没睡觉的人需要吃些热的东西;睡梦中的人在被子里寻找彼此的手,而他们的梦境变得更加清晰;报纸散发出墨香味,白天发出第一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