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也想做一个温柔的、温婉的、平静如水的贤妻良母,可是我做不到...还不如当个土匪,当个女匪”,自诩“爱情困难户”的当代女诗人余秀华坦白。
但越是爱而不得,越有反弹力,越渴望。从“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到“我在练习死亡”,余秀华诗性的荷尔蒙已经冲破了肉体和人生的枷锁,与生命的荒谬共生共存。在作家何立伟看来,余秀华拥有三重身份,她是农民、是诗人,是过着灵魂和宗教的生活的人。
“只有面对爱或想爱的时候,这是我唯一的自卑”。 尽管拥有了精神自由,余秀华仍然为现实所扰。她直言自己的诗歌创作陷入困境,也分享自己在上一段亲密关系中感受到的恶意与攻击,尝试去重新界定幸福的标准。在爱与不爱之间,她就这样“摇摇晃晃地活着,半明半暗地活着”。
在11月18日的平行诗歌节上,余秀华与何立伟围绕《与生命的荒谬共处》进行对谈,聊聊那些和诗歌、死亡与爱有关的故事。以下是对话的精彩内容回顾。

嘉宾:余秀华 x 何立伟 主持:天水
世界是三层楼的房子,
余秀华是里面的居民。
天水: 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平行诗歌节的第一场诗歌沙龙,我来简单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
何立伟老师作为湘军文坛的代表人物之一,创作非常丰富,虽然以小说成名,但实际上早年也写过诗歌,同时他也著有很多随笔散文,包括文学批评,这些年还有漫画作品问世。
另外一位是我们特别好的朋友,诗人余秀华,相信在座大家都很了解,我就不多介绍了。
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叫“与生命的荒谬共处”。我在想这个主题的时候,正好看到了秀华的一篇文章,叫《在半光明里继续写作》。那篇文章中她提到了加缪讲过的人生是荒谬的,以及她自己的生活和创作,常常就是这样一种存在的状态,与荒谬共处。在这一年里我们多多少少都在经历新的荒谬和面对很多东西,那么我最想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秀华你最近的状况、心态怎么样?先跟大家聊聊吧。
余秀华: 下午好,各位朋友,这次来长沙我觉得很开心,因为我和海蒂、天水一直是私交很好的朋友,她们知道很多我的事情。今年我自己也很糟糕,不管是生活上还是别的。不过现在都过去了(我又回归平静了),所以我的经历可能没有什么特别,我觉得我也说不出来。
天水: 刚才提到此刻的体验,在创作层面上,秀华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余秀华: 今年经历了那些事之后,我的诗歌创作就陷入了一个困境,写不出来,不管怎么写都写不出来。但我唯一坚持在写的是随笔,有时候是小说。诗歌到现在我是完全写不出,我不知道怎么去写,以后能不能写出来我不知道。
天水: 这个时候特别需要何老师,他的创作生命很长久,并且人生阅历也非常练达,请来跟我们讲讲在这种难免都会遇到的困境中,您的感受,您的想法。

何立伟: 好的。我先聊聊余秀华吧。昨天我认识的女性朋友,一个职业经理人,她知道我和余秀华会有一场对谈,就给我发了余秀华在上个月写的一篇随笔,叫作《先生,我想给你写信,说说我的贪心》,然后还发了她前两天写的两句诗。她说她读这篇随笔,是流着眼泪读完的。你还是感动了很多人的。我既是一个对谈者,也是余秀华诗歌的阅读者,通俗地说就是粉丝,所以见到了余秀华本尊,很高兴,但是她没有超出我的想象。
读文学作品的时候,我们会想象作者,但这是一个读图时代,网络上有很多余秀华的照片、视频,所以我就没有意外,她没有走出我的想象。而且余秀华是一个没办法粉饰的人,你没办法用想象去粉饰她。她很真实,就是这个样子。
刚才休息的时候聊天,我说余秀华和我都是楚人,因为古代湖北、湖南都是楚地,是有特别倔的文化性格的。余秀华身上就有楚人的性格。她在《在半光明里继续写作》里面也写了,她是一个不安分的人,她是倒着出生的,古人叫“寤生”。她来到这个世界从一开始就不老实,倒着出生,带来的恶果就是缺氧,造成终身行动不便、口齿不灵。但是这些后果并没有影响到她继续地不老实,她不安于现状。
她在2009年33岁的时候开始写诗,5年以后,2014年在《诗刊》发表了她的组诗。而发现她诗歌才华的人,也是楚人,是我们湖南人刘年,一个非常好的诗人。刘年看到她的诗以后,写了一段评语,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说她的诗歌放在其他女诗人的诗歌里面,就好像一个杀人犯走到了一群大家闺秀中间一样,那么惊人,那么不一样,那么有凌厉的杀气,杀进了诗坛。
我是一个有写诗的“前科”的人,我年轻的时候写过诗,后来成了诗歌的叛徒,转去写小说,就不写诗了,但我是一直阅读诗歌的。我读过余秀华蛮多的诗,她是一颗很灿烂的升起的星。我就奇怪:她为什么要写诗?她为什么选择诗歌?因为她的灵魂不老实,按她的说法就是不安分,她的灵魂要挣扎,要从肮脏的身体和世俗里面挣脱出来,要表达干净的灵魂。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勇气的。她的诗歌大胆地表达一个进入中年的女人的对爱情的渴望,对肉体之欢的渴望,包括对家乡、对故乡、对土地、对亲人……这些渴望在燃烧,成了她的欲火,欲火难平,所以不吐不快,所以她写了很多诗。她选择诗歌,是因为她有明显的过人的诗才。词语从她笔下流出来,就是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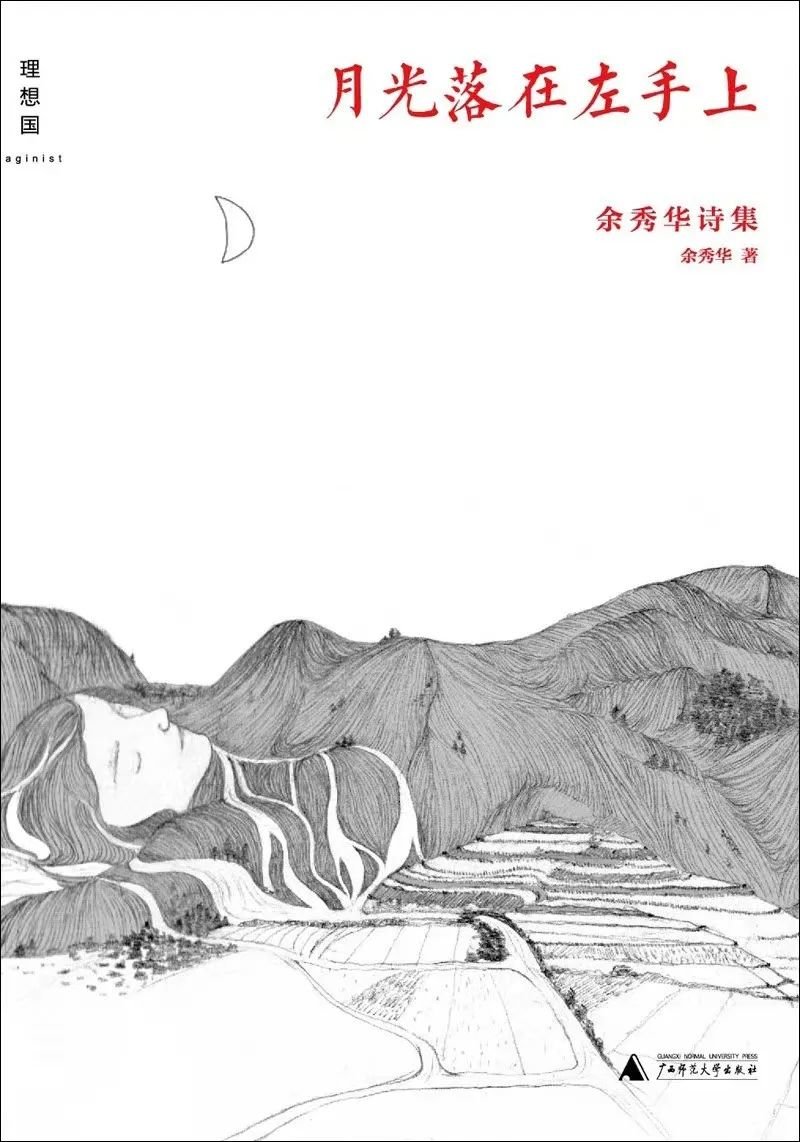
余秀华诗集《月光落在左手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2015-2
刚才说到《先生,我想给你写信,说说我的贪心》,她的贪心就是她的欲望,这篇随笔写得非常好,而且信息量非常大。她在里面写了“我最大的愤怒是对自己的愤怒,我是多么不争气”。我想问问余秀华,你现在不要回答,等我说完再回答:你的愤怒是什么?你的不争气是指的什么?
而且在这篇文章里面,她写“我摇摇晃晃地活着,我半明半暗地活着”。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前一句是坚强,后一句是纠缠,她又坚强又纠缠,就像今天这个主题——与生命的荒谬共存。这就是生命的荒谬。她前几天写的几句短诗里面,说她的心里面一边是妓院,一边是教堂,这句话也是荒谬的,也是生存的荒谬,人格的分裂。
在文章里她还重点地写了对生与死的思考,她写,“想着死亡是可以解决这些事情的”,她想用死亡来解决人生的困境。然后还有一句就是,“这撕心裂肺地活着,到底是为什么?”生和死的思考在纠缠着她。还有一句话,“我在练习死亡”。加缪说过一句话,意思是“哲学的终极问题就是如何思考死亡”,用我们长沙话来说就叫“想死”。那么,她为什么会“想死”?我觉得一个真正的诗人、真正的好作家,到达一定层次的时候,一定会思考人生的终极问题,包括荒谬,这也是终极问题,因为人生充满了荒谬。
我的一个朋友史铁生,是中国非常了不起的作家。他很年轻的时候得了高位截瘫,之后写出了代表作《我与地坛》。他每天摇着轮椅到地坛,坐在树下思考死亡。因为他被逼到了绝境:他活着的意义在哪里?他活着的出路在哪里?他必须思考,因为他每天都要面对。就是传达室老大爷问的问题: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你是谁?所以好的作家、好的诗人都是思考人生的终极问题的。
我很喜欢的散文家也是漫画家丰子恺先生,有一篇文章纪念他的老师李叔同先生。他打了一个比方,说这个世界是一个三层楼的房子,住一楼的人挤人,就像沙丁鱼罐头一样,都是为基本生存而挣扎的人。住二楼的人就比较少,这些人是为艺术、哲学或者精神生活的人。第一个是为了物质生活奔忙的人,第二个是超越物质生活过着精神生活的人。那么李叔同属于住在三楼的人,三楼的人寥若晨星,这种人是过灵魂的和宗教的生活的人。所以你过灵魂的、宗教的生活,你就会面对最终极的东西。
我觉得余秀华是这三种生活都过的人,三位一体。首先她的原始身份是一个农民,现在还是要为生存而奋斗,她是在一楼住的人;作为一个诗人,她也是住在二楼的,艺术、文字、审美是她的精神追求;同时她还跑到了三楼,练习死亡的人一定是住在三楼的。所以她是这三层楼的居民,有永久居留证有绿卡。
我觉得今天的题目非常好:如何与荒谬共存。余秀华在《在半光明里继续写作》里面也写了,认识了人性的恶以后,她觉得无可逃避,这种人性的恶包围着她,只能共存。我的理解,这种共存绝对不是一种和平的共存,它是一种抗争的共存。因为一个战士需要看见敌人,一把刀需要看见血,这就是共存。战士和敌人是共存的,刀和血是共存的,而且是一种荒谬的共存。
这种荒谬实际上是对人生的一种限制。余秀华面对的限制是非常多的,她在文章里特别提到了身份的限制——身份对人是有限制的,包括你现在把她称为诗人,这个称呼对她也是一种限制——对任何自由的灵魂来说,所有的限制都是荒谬的,她必须冲决它。余秀华是一个勇敢的人,她敢于呼唤、敢于释放,她一点都不加以掩饰。
她最有名的诗就是《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请问在座的这么多女生,谁敢喊出这样的话来?只有最勇敢的灵魂才敢说出这样的话,因为她有最勇敢的灵魂,她挣脱这种荒谬,和它共存,同时她冲破限制。我们每个人都是在限制中生活的,所有人都是戴着镣铐的人,但她是戴着镣铐跳舞的人。“戴着镣铐”和“戴着镣铐跳舞”是两个概念。对她,人和镣铐是共存的,她带着镣铐跳舞,挣脱了镣铐对她的束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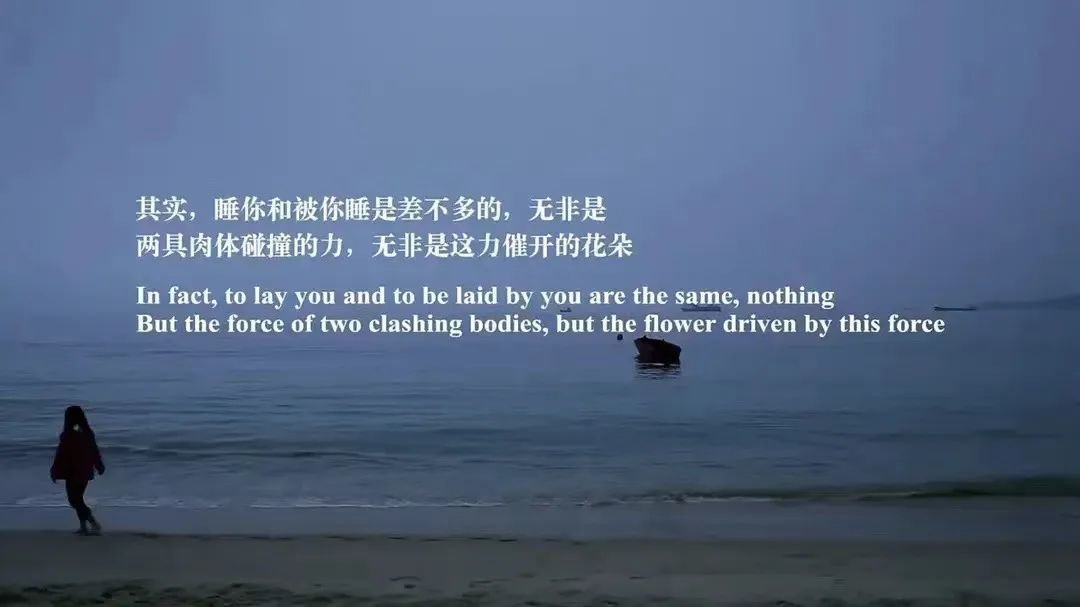
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
每个人写诗都会写爱情,但是很少有女孩子这么大胆地呼唤肉欲。 她有一篇文章我还记得,就是她的灵魂已经很充实了,任何一个男人都够不上她的灵魂的对手,那只能用肉欲来解 决。 所以这是非常大胆的,也是让我觉得非常有勇气的。 而且她写得不下作,她有一种人生的审美的高度,人就是要活出想要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勇敢的、挣脱的、灵魂高扬的一种状态,实际上她是呼唤一种自由,呼唤去冲破一切束缚、一切偏见的生活。
她就像一个吃低保的人渴望一桌好饭菜一样地去渴望肉欲。所以我相信她在感情上绝对是一个“爱情困难户”,她肯定是爱而不得的人,越是爱而不得,越有反弹力,越渴望。而且她绝对是一个诗性荷尔蒙非常旺盛的人,才能表达得那么有力度。如果一个人的诗性荷尔蒙不是分泌得这么旺盛,不会有这样的力度,这种精神的力度、呼喊的力度、燃烧的力度,像烈酒一样。波兰诗人米沃什说,诗人应该向同类表达人类最简单的善意。我觉得余秀华不但表达了人类最简单的善意,她也表达了人类最复杂的欲望。

只有面对爱和想爱的时候,
这是我唯一的自卑。
天水: 刚才开始之前,何老师一直说“我就随便说说”,结果我们可以看到他几乎写了一篇论文。同时也引出了一些问题,实际上秀华现在可以回答。
何立伟: 对。你的不争气是什么?你的愤怒是什么?
余秀华: 我的愤怒并不是指我的身体上或精神上,我对这个没有侧重。我是从上一段关系里看到了人的恶意,我在想我怎么也会变成这么充满恶意的一个人,我愤怒的是这个东西,倒不是别的。
何立伟: 你这是新的愤怒还是古老的愤怒?
余秀华: 新的愤怒。其实对我的身体,我一直是觉得还能接受。就像你刚才说我是爱情困难户,所以只有面对爱或想爱的时候,这是我唯一的自卑,其他的基本上没有自卑。今年经历了这些事后,我也觉得人世间总是要有很多的爱情困难户,这才是正常的。人世间要有像我这样的爱而不得的人,才是正常的,所以我一直去追求爱情,也是因为我就是想证明自己……
何立伟: 在不正常的状态里表达最正常的欲望?
余秀华: 对,我就想证明自己,哪怕我长得这么丑,我仍然能得到爱情。所以不是为了去追求爱情,而是为了证明灵魂的契合会高于身体的限制,结果我是失败的。就像很多限制,本来我们以为是可以轻而易举打破的,但是后来发现人的限制,哪怕很小的一个限制,对每个人的影响都是很大的。
我们说的人性之恶也不一定就是人性之恶。人类发展到现在,很多东西还是理解不透的,现在我想那也是一种美好的秘密,要我们去探索的。作为诗人,作为作家、画家、艺术家,这是我们需要真正去探索的东西。这是今年的这段经历带给我的不多的感受之一。
天水: 刚才何老师和秀华都提到了“限制”,或者说“被禁锢的”,所谓“爱而不得”。我想其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不管我们的身体是正常的还是有状况的,或者精神是什么样子的,不管我是美的丑的,可能人生的终极问题之一就是爱而不得,求而不得。
秀华因为她个人的体验丰富和她的勇敢,让她可以非常直接地将这种体验展现出来。一个人很难的是把自己那么残忍地剖开给世人看,然后我不在意。我相信秀华在得到了我们很多的朋友的爱的同时,也一直在巨大的公众的关注里面,有很多很难听的声音,会一直伴随着她。
余秀华: 一直。不管你怎么做,受攻击的永远是我。比如说我和正常的男孩子谈恋爱,别人说“你为什么不拒绝他“,错的是我。当我被打了以后,就是“你喜欢骂人,你活该被打”,错的还是我。无论什么时候,错的永远是我。
何立伟: 饱受社会攻击。
余秀华: 可能我就像刚才何老师讲的,(同时住在)三层楼,我面对的全部是一楼的攻击,第二楼基本上没有,第三楼就根本没有。这件事我如果说出来,他们又会说,“呀,你把自己看得那么高大”“你就是个会骂人的肮脏的女人”……我真的没有办法回避这些问题。比方网络上那些专门开小号黑我的比比皆是,他们为了骂我开了很多小号。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办,你怎么说都是你的错,哪怕别人打你都是你的错,别人没有错。
很多时候我想一想,毕竟我是个残疾人,好像我的很多举动,比如说《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这首诗,它挑战了一个正常人爱情观里的底线,就是违规。
天水: 因为这首诗受到了关注和喜爱,同时也受到了很多的攻击。
余秀华: 对,我发现那些没读过(我的)诗的,如果说到余秀华是什么诗人呢,就说她只会写“睡”,这就是认知的偏差。就是大致上他也知道,但是他不想去了解,他只要找到一个攻击的点就够了。
何立伟: 其实她表达的欲望都是非常正常的,但是那些所谓正常的人反而不正常地带跑了这些正常,所以说这也是荒谬。

很多人把所谓的幸福,
都标准化了。
余秀华: 就像我们刚才聊天的时候,何老师说我是一个不正常的人,就把这些东西正常化了。其实我想的是相反的,我是正常的,那些人是不正常的,这样才合乎情理。但是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男权打压女性,让女性变成自我的无欲。就像那些攻击我的人,说余秀华那么有名有钱有什么用啊,你还是没有幸福。我有老公有孩子,我相夫教子,我就是成功的,我就是幸福的。很多人把所谓的幸福都标准化了。
天水: 对,就像我们现代社会的成功学一样,你要拥有多少金钱,你在什么样的地位,就是成功的男人;你有什么样的老公什么样的孩子,就是成功的女人……
何立伟: 都有标准答案。
余秀华:如果你的观点和他不一样,他就会攻击你,说他是对的,你是错的。我觉得在这些事面前,我犯的错误是很小的。反正攻击我的人那么多,现在我已经对他们死心了。
天水: 刚才我就在想,当我们去面对“正常”和“不正常”的时候,可能每个人身上都有看似不正常的一面,生命的荒谬就在这些东西上体现出来了。而且刚才秀华特别提到,在中国身为女性,我们永远在面对社会上各种的眼光和要求,比如我常常会听到的身材焦虑、容貌焦虑,还有年龄焦虑。不管身体状况是否正常的一个女性,实际上都是共同在面对的,我也在面对,在座的很多女性朋友可能都会面对。但是恰恰是秀华把我们面对最直接、最赤裸的问题的时候的思考和自己的样态,用她的创作袒露出来,让大家看到。她可以打动很多人,就是我们说的共情。我记得秀华也讲过,她的诗歌会受很多人喜欢是出于共情,但是“共情”和“知音”之间是不一样的。
余秀华: 有很大的不同。能够共情和是不是知音之间有很大的一个鸿沟,能够和你共情的人很多,但能够做你的知音的人很少,几乎为零。
天水: 几乎为零?那么身边的好朋友,有创作上能够懂得你的人吗?
何立伟: 能够懂得你的,或者你的灵魂知音,应该还是有吧?
余秀华: 应该还是说,真的只是共情。而且一个人,如果别人能懂你,我只能说是你的失败。

纪录片《 摇摇晃晃的人间》
何立伟: 我请教一个问题:你写的《先生,我想给你写信,说说我的贪心》,那个先生是你虚拟的吗?
余秀华: 不是。
何立伟: 是吧?那么从那里面就看得出先生是一个懂你的人,是你的知音。
余秀华: 他可能就是你说的爱而不得。
何立伟: 那他就是一个懂你的人。
余秀华: 他也不一定懂我,哎呀这个……
何立伟: 但是你的文字表达出来,他是一个懂你的人。
余秀华: 是我懂他懂得比较多,因为我们认识了很多很多年。
天水: 在听他们俩这段对话的时候,突然想起我之前想的一个问题。何老师说秀华在文章里写到说我怎么那么不争气,同时也提到秀华其实是一个非常不服气的人。我本来想问,你现在还有不服气吗?然后我觉得刚才的对话和她讲的所有的话,都在回答我这个问题,其实她始终不服气。
余秀华: 到现在我已经服气了……
何立伟: 你永远不会服气。
余秀华: 我服气啊。
何立伟: 你是临时性的,都是假象。
余秀华: 我本来就是爱情困难户,你服不服它都是客观的,所以说我一定要证明自己,人的灵魂可以超越你的身体的限制,结果不对。很多人没有灵魂,你面对的都是鬼魂,是吧?
天水: 没有灵魂,所以你无法用灵魂去超越任何限制。
余秀华: 所以当他们看到这个人和他们不一样,他们就会群起而攻之。上次有人骂我说你看肯定是你不对,要不这么多人为什么会群起而攻之。然后我就打了一个比喻,我说本来一大群鸡,你放个老虎进去,那鸡会不会害怕和受惊?我说我是一个人进了鸡群,他们不认识我所以来啄我,这句话又惹了好多麻烦。
天水: 对,而且秀华的表达实在是太直接了,她用的很多比喻极其市井。
何立伟: 因为诗歌是含蓄的,含蓄的同时也是多义的,看你怎么理解,所以从反面理解她的诗的人特别多。
余秀华: 日常化的诗歌也有新意在里面。首先诗歌是你对人的理解,对世界的理解,对人性的理解,根本不是你(使用的)这些技巧,你的技巧都给我看到了。
何立伟:余秀华是一个让人很奇怪的人。我曾经看到她说她要左手按着右手,写一个字都是很费力气的。这么费力气写的诗,却那么轻柔。
她的诗才非常好。刚才我们聊天,我说进入诗歌是有秘密通道的,很多人没有,进入不了。写诗,古人说“诗有别材,非关书也”,和你读书没有一毛钱关系,你就是读了博士你也写不好诗,写诗需要特殊的才华。
刚才说了我有写诗的前科,我在八十年代初期,在《人民文学》、在《诗刊》、在《新星》等都是发表诗,发了100多首。但是我编自选集的时候唯独没有把诗歌收进来。而且我在自序里面写了,我认为那不是诗,我对诗还是看得很高的。有很多诗、很多诗人,我在心目中给了他一个标签,这是“伪诗人”,他写的诗我称为“伪诗”,那不是诗,那是有着诗的形式的普通的句子。
余秀华有非常高的诗才,她那种句子,包括她打的比喻,很多我觉得都是神来之笔。她写得很艰难,但是写出来之后其实你读得很轻松。虽然内容很丰富,但是读上去绝对没有障碍,尽管她写的时候是充满了障碍的。所以她这一点让你很奇怪:这个人怎么会有这么高的诗才呢?
关于诗歌,余秀华在她的《在半光明里继续写作》里面一再地说,她自己都不知道什么叫作写作,另外,余秀华为什么会开始写诗?而且一下就爆发。诗人早慧,很多诗人都是很早就开始写诗,比方骆宾王七岁就写了著名的“鹅鹅鹅”,但她到33岁才写诗,37岁才发表,很迟,为什么?而且一出手写得那么好,风靡全国。
天水: 那扇门是怎么打开的?
余秀华: 我不是突然爆发的。我读初中的时候要参加校园里的一个文学比赛,别的同学写的是文章,我心里想写个作文那么多字,我就写写诗歌吧。
我模仿艾青的《望星空》,其实也不是模仿,也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形式是模仿艾青的。当时我得了唯一的一个特等奖。
何立伟: 所以你说你很早就开始写诗。
余秀华: 开始我是为了参加比赛,因为我写字很困难,没有办法,真的不想搞这个(作文),所以写点别的,如果不合格就算了。
何立伟: 余秀华还有很多的奇怪之处。有一点奇怪是,她没受过高等教育,也没读过中文系,但是她的思想是非常成熟的,情感也是,有的时候虽然鲁莽,但也是成熟的鲁莽,不是那种少年义气的鲁莽,而是一个正常女人的有力度的呼喊。我不知道她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自学的,你读她的诗歌也好,文章也好,会发现她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个人的而且非常成熟的认知体系和价值体系,这也是让我非常好奇的地方。
余秀华: 我没有价值体系。
何立伟: 你怎么没有价值体系?非常鲜明的。
余秀华: 而且我不知道什么叫价值体系。
何立伟: 你不承认是不行的。
余秀华: 不是,我不知道,真的。我是从小就喜欢阅读,到现在都是认认真真一本一本一字一句地读,包括小说,我从来都是精读,不是泛读,每一本都精读。
何立伟: 不是泛读是精读,但是你读的书肯定不少。
余秀华: 每一本都精读,所以每一年读的书最多30本。有的人读100多本,我最多只能说30本。
何立伟: 精读30本也不少了,精读一本可能相当于泛读10本。
天水: 今年读了多少本?
余秀华: 今年差不多快30本,暂时不到,差一点点。

诗太难写了,
但诗又是特别准确的一种文体。
天水: 谈到读书,何老师说秀华身上有她的才情,我们姑且称之为天才的一面。同时秀华刚才讲的,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之间,她其实已经在建立和创作之间的桥梁。无论是通过阅读,还是小时候因为身体的原因,写作文太费劲所以用诗来表达。其实诗是非常难的,像何老师说的,诗太难写了,但诗又是特别准确的一种文体。
何立伟: 你看我发表了100多首,我都不认为那是诗。
天水: 我的想法是这样,我们常常说每个人都可以有诗意,也可以追求诗性,或者我们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我在写诗”,但你是不是真正的诗人,它是否成立,这背后其实有技艺、技巧,以及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内在的天分、天赋。
另外一个我一直想问的问题,也是何老师有提到的。我们面对各种人生状况的时候,常常会说一句话, “我和自己和解了”。我不知道这是一种消解还是一种和解,每个人看着都特别和谐。我们是用这种方式去共处的,但何老师说秀华的共处是抗争的共处,所以才能从她的作品里看到很多我们不敢做的,但是我们可能也遇到了的情况。其实不只是秀华,任何一个女性,或者说任何一个人在感情中,都可能都会遇见同样的事情。我们会遇见渣男,我们会遇见不是那么符合自己灵魂渴望的爱情,但是没有多少人在这个过程中如此地把自己的挣扎、抗争表达出来。甚至刚才她说,我觉得自己不争气,是因为我竟然暴露出了人性之恶。
何立伟: 我觉得这挣扎有一种是自觉的,有一种是不自觉的,本能的挣扎也有,但是余秀华更多的是一种自觉的挣扎。
天水: 对,其实她是带着非常强大的自觉性和思考在里面。但我真的有一个问题,你觉得你是抗争的吗?你是在抗争地和荒谬共处吗?你自己怎么看?
余秀华: 别人老说我是抗争的,但在我自己的意识里是没有这个观念存在的。我觉得这就是我本能的性格,并不是我主动地去抗拒,我没有。唯一的抗争可能就是我的婚姻,因为确实太不喜欢,所以这个抗争我觉得是有的。其他的,社会上的事情,好像他们骂我我就要骂回去,我觉得这真的是性格问题。
何立伟: 她说她的反抗是性格。
天水: 是性格使然,天生就是忍不住,憋不住。

Q:读者提问
好诗是一面镜子,
能照见你也有同样的情感。
读者1: 刚才老师们谈到了“限制”“残疾”,我觉得残疾这个定义并不只是您的标签,我们每个人都是残疾人。残疾就是一种限制,残疾人会因为身体的不便产生迷茫,我们所有的人也会因为自身各种原因遭受限制的时候产生迷茫,所以我们都是残疾人,所以我在读余老师的诗的时候有一种强大的共鸣。我从本科到研究生都一直有写关于您的作品的论文,我觉得有您这样一位真正的诗人能够陪伴我的阅读,今天甚至能与您面对面交流,真的是非常荣幸也非常感动。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冬天的季节,真的除了所谓的爱情,就只有诗歌才能够温暖我们。
想问一下余老师和何老师,对于我们写诗的青年人或者说读诗的青年人,有什么建议?怎么样读诗或者应该怎么样写诗?
何立伟: 我建议你看一下何小竹的诗,他是我心目中很了不起的一个诗人。首先,何小竹诗写得非常好,另外,他不断地推年轻的诗歌作者。年轻人最怕是没有判别能力,疑似诗你也认为是诗,那读了等于没读,而且会破坏你的诗歌审美。何小竹就是一直在推真正称得上是诗的作品、真正称得上是诗人的作者,他们的作品一组一组地发。
我觉得年轻人首先要读真正的诗,真正的好诗,然后如果你有诗歌的潜质,会在读好诗的过程中被激发出来,你没有这种潜质,你就只能成为一个阅读者,因为诗歌这东西一点都不能勉强的。所以一定要有一个自我的度量,一个自我的把握和评估。我是不劝年轻人没有诗才还硬写,那是害他。
所以第一要读好诗,第二要评估:我如果热爱诗歌,我也想写诗歌,我有没有这个潜能?人有各种可能,你完全有可能成为诗人,只有在读到好诗的时候,共情、共鸣的时候,你才能发现你也有这颗诗心。人家的好诗是一面镜子,能照见你也有同样的情感。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也有这样的诗意和情绪,那你就可以写诗了。
余秀华: 这个问题何老师回答得已经非常好了,所以我同上。

只有文字能够把你对自己,
或者对世界的认识清晰化。
读者2: 我想问一下余老师,您一直有一个强大的精神力在不停地创造诗歌,感觉您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人,请问您是如何保持这种力量的?
余秀华: 我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不一样,或者说自己感觉不到。我只觉得诗歌的存在是一种生活的日常,就和打麻将、喝酒是一回事。我喜欢写诗、你喜欢打麻将、你喜欢喝酒,这道理是一样的。所以诗歌在创作过程中,它的形式不会比这些高,但它作为文字是可以留得下来的,可以说这是文字讨巧的部分,同时它也是一种对自己的认识的清晰化。你开始对自己有各种各样的认识,但都是模糊的,只有文字能够把你对自己或者对世界的认识清晰化。
比如我是近视眼,如果我不戴眼镜,我看你们全部都是一片模糊。我戴眼镜就是写诗歌的过程,把这个记下来,它更多的是对自我意识的一个清晰化。
天水: 刚才秀华说了一个非常精准的比喻,就像我为什么戴眼镜。我写作,创作诗歌,就是对自我的清晰化,我要看得清楚我自己。
余秀华: 就像何老师刚才提到我的随笔《先生,我想给你写信,说说我的贪心》,我是真的写了这个文章之后,一下子就从之前那段不堪的回忆里走出来了。我开始回忆,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他想要的是什么,我是不是真的爱他,他是不是真的爱我。然后我也分析,我觉得都不对,一下子就出来了。很简单,想清楚之后,这是一种自我认知的清晰化。不管有多美好或者多丑陋,只要你的认知是清晰的,就能够走出来。
天水: 清晰是一个比较精准的状态,你也不过分地去美化美好,你也不会过分地去丑化丑陋,它清晰了就好了。
余秀华: 天水一直说,为什么我愿意把自己剖析得那么深刻放在大众面前?首先我是觉得,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一颗尘埃,你装逼是没有用的。而且对我个人来讲,我不想在社会人际关系里获利,我就没有必要去装。我剖析自己也是为了清晰自己,所以我觉得社会上如果都去装逼,社会的存在就没有价值和意义,必须有几个像我这样的不怕死的人去清晰化。清晰化自己也是清晰化很大部分的“人”,因为人性相同,人性相通,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好。余秀华很好。

我的多巴胺还没有用完,
所以还是会谈恋爱。
读者3: 余老师您好,我只有一个问题,想知道您以后还会再去做关于爱的实验吗?
余秀华: 对自己的性格我是最了解的。经历了那么痛苦的事以后,我觉得暂时可以放下,但是保不齐明年后年我又蠢蠢欲动。何老师觉得我永远是一个不会安分的人,这我是真的没有办法,这是性格决定的。我也想做一个温柔的、温婉的、平静如水的贤妻良母,可是我做不到。我觉得贤妻良母在我眼里一钱不值,还不如当个土匪,当个女匪。
读者3: 我更希望您以后可以爱得轰轰烈烈,就不需要做一个温柔的人。
余秀华: 我的天呀,爱得轰轰烈烈,死得悲悲切切。
我本来就是爱情困难户,现在年纪又大了……网上也有人说余老师你还要爱情干什么?我说如果我到了80岁,还能找到一个20岁的,那可就牛逼。青春少年都是美的,美女俊男谈恋爱不值得羡慕,这是人之常情。你如果到了四五十岁还能认真去爱,而且不考虑什么人际关系、金钱,那是第二牛逼。第三牛逼的是,像何老师说的爬到三楼上,80岁的时候,你还能和一个20岁的小伙子睡觉,那如果不叫爱情,其他的也不叫爱情。
天水: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差不多,每一次失恋的时候都说我再也不会爱了,但是保不齐什么时候就又蠢蠢欲动。
何立伟: 荷尔蒙不消失,这个事情就不会终止。
余秀华: 何老师,女人的多巴胺和男人的荷尔蒙是有定数的,我的多巴胺还没有用完,所以还是会谈恋爱。
天水: 没错,不要拿年龄、不要拿各种东西去限制爱的能力。爱的能力是生命力,我们在活着的时候,这个能力存在,就应该为此庆幸,而且感激。

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
嘉宾简介:
余秀华, 中国当代女诗人。代表作《月光落在左手上》《摇摇晃晃的人间》《我们爱过又忘记》《无端欢喜》等。
何立伟, 生于1954年,长沙人,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出版有《小城无故事》《像那八九点钟的太阳》《亲爱的日子》等二十余部小说、散文集。
天水, 诗歌岛主理人,文学策划人,策展人。
相关:
读懂摩洛哥足球发展轨迹,他们的经验和日本队一样虽然半决赛0-2不敌法国,但摩洛哥队已经震惊了世界。任何世界杯赛场的狂飙疾进,从来都不止有实力和运气的双重加持,之于摩洛哥而言,他们只是把一件正确的事情,坚持了至少10年:那就是尊重足球的基本规律,用最..
姆巴佩要技术有速度?可别小瞧了“姆总监”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一句揶揄姆巴佩的话——“姆总监要技术有速度,要能力有速度,要战术素养有速度”。似乎,姆巴佩除了速度一无是处……但是这届世界杯和这场对阵摩洛哥的半决赛,姆巴佩再一次无形中决定了比赛。..
